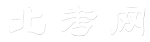对着风景,微笑不止散文
卖油饼的女人
每天六点五十我出门,开车驶出小区赶往学校。
时间久了,便发现了有趣的事,同一些人会在同一个时间重复同样的事。比如下了楼,经过车库门口时,会遇着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看门人,总是和胖老婆拉着垃圾车,一前一后去垃圾点;烫发的女子拉着背大书包的小姑娘,孩子撅着小嘴眯着眼跟着大人高高低低地走,她还没有睡醒;再走几步,一对花白头发的老人提着一篮蔬菜慢慢踱步过来,只是这篮子里的菜天天变化,有时是几颗洋芋,有时是一颗南瓜;到小区门口时,卖馒头的女人正揭开笼盖,笼屉高达十几层,白茫茫的热气把馒头香味送了过来……
卖油饼的摊子就在馒头铺隔壁,脏兮兮的店铺,女人总是边炸油饼边大声喊,“油饼出锅了”,清脆的少女声音,不停吆喝“热油饼嗳,热油饼嗳……”,一声未平一声又起。人们呼啦啦聚拢上来,她麻利地收钱找钱、扯下黑塑料袋递油饼,动作娴熟流畅,人群便又匆匆忙忙四散而去。
这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个头不高,围着黑褐色塑料围裙,因为特胖,看上去更矮。她麻利地照顾着生意,大眼睛扑闪扑闪,脸色常常发红,映衬得白帽子更加雪白。
周末的清晨,去店里买油饼,见她和三个女人正在搓麻花。案板上,一大堆面团泡在油汪汪中,油碗清亮亮,小小的MP4里放着凤凰传奇的歌。她边搓麻花,边扭着胖屁股在地上转圈,揉成细条的面和肥胖的身子一起晃动,三个人大笑,脸庞是向日葵般的饱满。
每天早上,她在架着油锅的门口忙碌几个小时。走过门口的人们,似乎每个人都会停下来买一份。无论人多人少,她也不急不慢,和蔼地笑。
卖油饼的女人,总是会在油饼剩下两三个时停下来,仰着头看三楼的阳台。
三楼的阳台上一定会出现一老太太,佝偻着身子,全白的头发。她喊,田姨,我给你送上来?老太太说,那太麻烦你了。她笑笑,没事,我正在减肥呢。
一问一答,每天都这样。
有天早晨情况发生了变化,老人没有在阳台露面。她喊了几声,没有声音,就有些慌,退后了几步,伸长了脖子喊。空荡荡的阳台上,玻璃被花花绿绿的纸糊得严严实实。她有些焦急,大声喊。一会儿,从窗子上坠下来一个小篮子,一根细绳儿,细绳的顶头系了一个小夹子,夹了二元钱。她笑笑,将钱取下来,把油饼仔细地裹好,然后才抬起头说,好了,您今天吓坏我了。老太太探出头来,狡黠地笑,我看你早上累得很,下雪了楼道滑,别跑路了,吊两个油饼上来吧。她说,放心,我给你天天吊油饼。走开几步,站在那里看老太太从窖里打水一样,将油饼提上去。人们都抬头看,都笑,这一老一中也笑。老人豁了牙,一笑露出黑乌乌的嘴。
后来,从阳台上垂下来的绳子上会系上一袋牛奶,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棒棒糖。有天天气奇冷,正好垂下一个手织的围脖。这些东西都是安静的,可看上去都像是有温度一样的。
不久孤身的老太太去世了,楼门口摆了几个花圈,还放了一张老太太的照片,年轻时的,笑眯眯真好看。那天早上,卖油饼的女人早早收了摊子,她脱下围裙,梳了头发,换上干净的衣服,走进三楼那家,拿出两个油饼放在照片面前,认真地鞠了三个躬,走了。
次日再次吆喝时,声音里就多了些悲伤。
她依然在小区门口卖油饼,每次剩下两三个时,总会停下来,抬起头看三楼的阳台,然后目光一点一点朝下移,好像那里还有一根绳子。人们也会跟着她看看那个阳台,那里再也没有垂下过细绳儿。
最近路过,已不见那买油饼的女人了,油饼店变成了卖保健药的小店,录音机铺天盖地的吵,“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阳光,永恒的徜徉”。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每次路过,总是还是想看看那矮胖的影子,想听听那清脆的吆喝声。
路灯下的等待
路灯从来都站那里,一声不吭,对身边的事却一目了然。有排排道旁树作伴,枝叶荫护,像是在抚慰彼此的心情。
清晨的路灯,总有些慵懒,还没来得及整理后脑勺的乱发,睡意未曾消去,白惨惨照着。当启明星升起,曙光微露时,路灯醒了,睁开眼看一看路过的人,然后继续酣眠。
黄昏时分,路灯像娇羞的少女,绽放着柔媚和温情,不似深夜时的凛然,也不像清晨时的黯淡。人流就是一群群蚂蚁呀,不断地聚集分散,各有去处,他们在灯下急匆匆走着,然后被不同的路带到不同的方向。
我在路灯下等某人,忍不住伸长脖子一遍遍看远处,虽知她一定会来的,但还是有些焦虑和埋怨。候人不至的心情,如同王维的《待储光羲不至》:
重门朝已启,起坐听车声。
要欲闻清佩,方将出户迎。
晚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
了自不相顾,临堂空复情。
百无聊赖,我抬头看路灯,路灯也看着我。它说,等待的时候,不妨看看听听身边的风景吧。
于是我慢慢地听和看。附近小店里飘来了米饭的香味,面汤的清甜;洗车店里一段段流行音乐,高亢得恰似锅里的滚水;几个冻红了的脸蛋的孩子,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嬉笑着经过;两个白发老人一前一后踱步过来,不言不语;穿大花裙拎大包的姑娘,一路摇曳走过。这情景,都会让人想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巴西民歌《在路旁》里的一段: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
路灯之下,有等待,也有分别,免不了翘首以待,也免不了目送远去。当然,也有争吵和谩骂,埋怨和仇恨。
总是有好多细微处让人感动。雨中灯下走路,疾驰的车辆及时刹车,轻轻驶过;雪天灯下路滑,醉酒的男子喊一声小心,全然不顾自己跌倒在地;某时还在灯下遇到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彼此意外,惊叫,寒暄,微笑。
闹市里,路灯下等人时往往会看见水果摊,水果差不多都摆在门口,各色的都有,酸甜的都在。我喜欢看葡萄摆在一起的样子,一颗颗如珍珠,紫色绿色黑色的摆在一起,仿佛玛瑙在聚会。也喜欢看两轮车上架着汽油箱改制的炉子,烤红薯或糖炒栗子,一阵微风吹过,一街糖风,一路甜,那么好。
这座城市,变化很快。经常在路灯下等待,会遇见好多熟悉的面孔,但每次还是觉得新鲜。比如一个哭着不想上学的胖娃娃,不久就成了瘦削沉默的大孩子。比如一个风华正茂的男子,不久就白了头发弯着腰独自转悠。比如一个妙龄的女子不久就变成腰身粗壮的中年妇女跳着广场舞。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可是他们跟别人说话。小城真小,转圈的时候都是熟人,于是,也知道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事情,或许他们也清楚了我的一些生活。
路灯下,人们等待或走开,春天,或者冬天,晴,或者雪。我们也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会遇上各式各样的路,不管等多久,不管如何迂回,结局是一样的。
这样想,路灯有点不是路灯了,就像是故友,它在那里,看着你我他。
墨水的墨
在文具店买笔,出门时,听见一孩子指着墨水瓶问,这是啥?
老板老了,白发,矮胖,摇晃着走过来,这是写字时用的墨水呀。你看,蓝色的,黑色的,你们上学不写字?孩子羞涩地笑,怎么不写,都写晕了。可我们是拿中性笔写的呀。
老人有些着急,挪过墨水瓶,拧开盖儿,把小瓶子摇摇。瓶子掉在地上,墨水四溅,一汪蓝洒开来。店里人都看,像看着蓝色的湖泊。老人回头问,怎么学生都不认识墨水了?另一个挑选日历的青年说,不用钢笔了,要墨水喝呀?老人笑起来说,肚里没墨水怎么行?孩子显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看着一地墨水,神情有些涣散,那种蓝像是灼伤了眼睛。因为很久之前,有一瓶纯蓝墨水,是多么令人骄傲自豪的一件事啊。
那时候,钢笔还是个稀罕东西,只有工作的人衣裳有四个口袋,左上衣袋的袋盖儿总是留个小孔不缝起来,干什么?插钢笔用的!
“我啥时有支永远不坏的钢笔就好了。”同桌低着头边吸鼻涕,边使劲抡起钢笔甩。他手里的'钢笔三天两头坏,不是笔头磨得不出水,就是出水一大滩,染脏了本子和手。字也写得七扭八歪,大金牙的语文老师总骂他吃了鸡爪子,写字呢还是画字呢。他也总是被罚站或写几百个同样的字。
“我最恨墨水的墨,这么多的笔画!”暮色渐浓,夕阳落进西山,他仍然在教室里吃力的画那“墨”字。我们饭都吃完了,玩都玩累了。
供销社里有钢笔,但很多人都买不起,好在有蘸笔头卖,也便宜,几分钱一个,班里很多同学卖回来,削个细树枝装上就成。墨水也贵,更是买不起,好在有一种叫墨水精的东西,几分钱一小包,指甲盖大的一点粉末,却能兑成一斤墨水。
相比墨水,墨水精写字模糊不清,写的字一会儿深一会浅,大小不均,还容易堵塞笔尖。有天老师经过时,同桌照例抡那破钢笔,甩了老师一身。新买的的确良衬衣呀!老师一耳光扇过去,他坐在地上大哭。老师说你还哭,一看你就不是个学习的料子,肚子里没一点墨水。
下课了,他忽然抱起墨水瓶就喝,喝得嘴唇乌青,牙齿乌青。我肚子里有墨水了,咧嘴笑,那笑也是乌青的。
过了几天,他拿了一支新钢笔来上学,还端来一瓶纯蓝的墨水。红色的钢笔,俊俏的像个姑娘,“英雄”牌的。墨水的颜色很匀称,恰似俊朗的少年,阳光照耀下,闪烁着梦幻般的色彩。他得意洋洋地大声宣告,钢笔比蘸水笔写字的感觉好多了,像什么呢?像顺着河水的小船,要多轻快又有多轻快。我也能写出一笔好字。同学们围了一圈,羡慕地看那红钢笔蓝墨水。
下午,白瑞怒气冲冲地站到我们桌前,“这是我的墨水,我的”。她是外地人,随舅舅在这里读书,因此是班上第一个拥有钢笔、最早有整瓶墨水的人。说普通话,也不像我们把头发扎个麻花辫,而是用缠了红丝线的皮筋把头发扎得马尾巴一样的,跑起来,上下飞晃着,晃得男生们的眼光能拧一股绳。
她一生气,班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这墨水是我的,被你偷去了。
墨水是我的,是我叔叔从西安带回来的。同桌涨红了脸,一拧身子站了起来。
谁能证明?我的纯蓝墨水瓶怎么不见了?没人证明,就是你偷去的。
同桌抬起头,瞪大眼睛,XXX可以证明。忽然指着我,或许是觉得自己经常给我好吃好玩的缘故,满含期待。
我看了看周围的人,也看了看他。这平时低着头,怯怯地,手上糊满了墨水的人,模样怎么看都像个贼娃子。时间似乎凝固了,很长很长,被信任的负累,聚焦的惶惑,我终于艰难地说,我可不知道。
老师来了,不说话,好像他也相信只有白瑞能拿那么漂亮的钢笔和墨水。
他颓然坐下,头埋进两腿间。哭,很长时间。接着就眼珠发直,浑身抖动起来,嘴里白色蓝色的沫子淌出来,黏黏糊糊一大堆。
我们吓愣了,大叫,四散,哭喊。老师来了,抱起就掐人中。他醒了过来,疲倦地躺着,但不说话。
第二天,同桌就不念书了。据他家人说癫痫病犯了,很严重。他妈妈追到学校问原因,可我们谁都不说,老师也不准说。
不久以后,父亲工作有变动,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和同学一起路过他家,记得坡上有很多杏树,家里有很多娃娃。大点的妹妹虽脏得像枚小镍币,但长得很漂亮,有明亮的黑眼睛,污垢之间饱满的小嘴,红得要滴出血来,坐在屋门口的一堆瓦砾上,抱着个更小的娃娃哄睡觉。
我们还看见,屋里的箱盖上,摆了一排墨水瓶。红蓝色的液体,映照着阳光,骄傲地发出璀璨的光芒。还有用完了的墨水瓶,倒上煤油,用棉花做捻,做成一盏盏的煤油灯。
他热情地搓着手,匆匆端来一些好吃的东西,问了很多同学的情况,仿佛那些误会和伤害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没有吃,起身告辞。秋风里,远远瞥见瘦削的影子伫立在旷野里,那鸟窝样的头发,向天呐喊。
再一次见面,已是中年人的聚会。都是忙于红尘,忙于寂寞之人,好多年没有见面,大家喝酒叙旧,说百般无奈,诸多不顺。怀旧童年少年,他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一再犯病,几次险遇死神。没有娶妻,当然也没有生子。地被征了,没有了家。钱被弟兄们骗完了,就扫地出门,靠低保过日子。
有同学自告奋勇开车接了他来。进了门,骇人一跳,憔悴苍老,眼斜口歪,脸上的皱纹像是故意雕刻,黝黑的脸庞印满了岁月的烟熏火燎,少许花白的头发夹在并不稠密的黑发之间。不干净的袄子上,缝着一块白布:我是患有癫痫的病人。如果我犯病,请通知我的家人。谢谢好心人!联系电话:xxxxxxxxxxx。
白瑞走了过去,抱着他的肩膀,眼泪一滴滴,几十年的。他嘿嘿地笑,一点也不伤感。说我长大了,头发长了。说白瑞长胖了,长黑了。
KTV里五彩缤纷,缓慢摇着的光,带着高处的尘埃,把他和他的影子层层掩埋。他坐着,喝开水,看大家拼酒唱歌说当年的许多事,叽叽喳喳,其间也说起他的将来。他倒是挥挥手,心无芥蒂地笑,仿佛自己这样的生命,本就不值得延续。
我们看着他,深知伸出手,也不会看到伤痕,却在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所以只有泪水没有哭声。灯光伸出温暖的手臂,却无力抚慰一个人多舛的命运。无论怎样,这些被时光遗忘的人,缭乱的世界已挽回不了曾经的过错。
朔风瑟瑟,树叶飘零,简单的碎片,常常徘徊。悔恨旋起一阵风,果子无声地落下来,在心中砸出深深的伤口。
忆及小学校,身边那个留鼻涕的孩子大声读“秋天来了,大雁南飞。一会儿排成横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还有他结结巴巴在复述列宁的故事:列宁被捕了,在牢房里坚持斗争,把面包捏成墨水瓶样子,然后把牛奶倒在里面,蘸着牛奶在纸上写字。纸片传出去后,他的战友用火一烤,字就显出来了……
还有一幅画。夜色渐墨,夕阳沉入西山,一个孩子在教室里吃力的写几百个同样的字。
“我最恨墨水的墨,这么多的笔画!”……
相关文章
忆清明散文2023-06-01 23:27:02
散文欣赏又是一年清明到2023-06-13 06:48:51
一条河的风景抒情散文2023-06-14 20:07:57
断魂清明日散文2023-06-19 15:52:31
人生中的雨散文2023-06-15 04:20:25
最温暖的风景散文2023-06-12 02:32:0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对比哪个好(排名分数线区2024-03-31 16:25:18
河北高考排名237950名物理能上什么大学(能报哪些学校)2024-03-31 16:19:2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山东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5:16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2:5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09:19
安徽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招生人数和最低分2024-03-31 16:04:52
醉翁亭记主旨句2023-06-17 14:25:36
醉翁亭记读后感(四篇)2023-06-05 01:46:10
醉翁亭记教案范文集合十篇2023-06-19 05: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