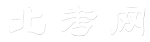一河旧时光散文
一
记忆是一河旧时光。小桥流水人家,厢房草顶,我家旧屋临河而老。夕阳西下,暮归的农人赶着牛马车从栅栏前的土路悠悠而过,把满身疲惫扔在斑驳的车斗里。晚风拂来,疲惫便随风飘散到暗红色河的褶皱里。
人流声、车马声,渐次稀少,一声清脆鞭响,让有些颓唐的村子委实激灵了一下。“得驾”,响亮的催喊声,“哒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谱成一曲乡村暮归调。不用问,是二伯踏着夜色归来了。在所有赶车人中,他总是最晚归来的那一个。他贪恋土地的温软、庄稼的丰泽,是种地能手、高手。他似乎是为土地而生,敬着土地,侍候着土地;土地供养着他,再荒芜,再贫瘠,经了他的手总会蔓延出丰收的态势。
土地入户后,春夏秋三季,从黎明到黄昏,二伯靠着铁打的身板在土地里摸爬打拼,盖起三层青砖红瓦房,三个儿子都在最佳年龄娶妻生子。二伯顺利完成了作为父亲的神圣使命。
我的村庄是一个农业大村,大队统领8个小队,按照自南而北的顺序划分,我们属于一队,二伯是生产队长。那时大伯是大队干部,他了解自己二弟,肯吃苦、懂土地,为人性情豪爽。当上小队长的二伯着实让大伯脸上光亮了很多年,他的能力远远超出大伯的期望值:有求必应,一呼百应,有极强的凝聚力。一队生产队长,这个最基层的岗位,他一干数年,直到年龄渐长,力所不能及,光荣退休。
微雨后的清晨,庄稼人还在头天劳累的酣梦里,一嗓子响亮惊醒桥边农户、桥下流水。“各家出个代表,都来小桥上开会。”不多会儿,叼着旱烟卷儿,敞着汗褂子,趿拉着鞋子,人们从各家门口惺忪而出。也有起得早的,梳洗干净,一脸清爽。雨润过的桥面洁净,少了浮尘,桥上石板光滑干净,桥下河水清灵,自北而南愉悦地流淌。四野飘来的尘土味、烟囱里轻软的炊烟气和破门而出的米饭香,弥散在这个清晨。
沉睡一夜的石桥突然热闹起来。吐着粗话,说着段子,年轻些的推推搡搡动手动脚,惊跑了桥下游鱼。桥东边,几个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当家理事,聚在一起,叽叽喳喳个不停。“都别说了,今儿开会商量事儿呢,村里吵吵得正热闹呢。”二伯故意顿一下,如定海神针,桥上瞬间鸦雀无声。继而,抬高嗓门:“这回分地是真事,政策下来了,15年不变,全村的土地按人头平分到各户。以后,土地是自个儿的了,都好好侍弄。咱村每人两亩多些,各家按人头算算自家分到的亩数。咱队就南北两块地,南边道儿远,地肥垄长;北边近,垄头短,有些地差了些。谁家赶上不好的地,一亩半顶一亩,抽签定地,赶上哪儿算哪儿,谁也甭耍赖!大伙儿看看,谁还有啥说的?”有三四个人,头抵在一起嘀嘀咕咕低声商量,仰头,拉开一副想申辩的架势,可眼瞅四下没人敢言语,又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没意见就散了,明天早晨再来,抽地。”人群在热闹中散去,几个不安分的后生,捡起石子,投下美丽的弧线,桥下的身影随着涟漪一圈圈放大,终归模糊不见。
那次分地,我家抽到了顶差的那块,东边挨着村里的坟地。边沿处,荒草蔓延,吞噬着青苗。更要命的是,不论哪家死了人,发丧出殡入坟地,都会踩烂许多青稞。若是赶上秋黄时节玉米成熟之时,许多秸秆上的棒子,还会经常被一些不安分的人顺走。父亲满脸不高兴,私下找二伯理论。二伯拍拍父亲的肩膀,眉间挂着一抹微笑,像一个大肚能容万物的活菩萨。“总得有人抽到这地吧?自家兄弟,啥都不用说了,产量低时,二哥给你补上点儿。”父亲也是个明事理的汉子,听二伯说到这个份儿上,便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二
上了桥,北边是生产队的场地,它的繁华和热闹在麦秋时节。骤雨初歇的清晨,朝阳早早把狂热挥洒到乡村,麦场上蒸腾起一团团白色雾气。早起的看场人在场上铺上厚厚的麦余儿,让它们饱吸湿雨之气,待到晌午,扫起成堆,晾晒一会儿,场地就干得差不多了。揭开麦垛,任骄阳吸纳其间的潮气。一切准备停当,只为晚上的麦场大战。麦秋,白天和晚上的时间都是金贵的,抢收麦子,在一场又一场突然而至的暴雨前。白天割麦拾掇地,打麦只在晚上。晚饭还没利落,二伯就喊上了,“紧紧儿地,都出来打麦子喽!”最先响应的是四叔,手里擎着旱烟袋,吧哒着烟蹿出屋门。其他人砸吧着嘴,似乎还沉醉在柴火饭的香甜里,也毫不迟疑上小桥,进麦场。
二伯和四叔这哥俩在麦场上总是打冲锋,轮流站在打麦机入口处,一个在最前边,紧挨打麦机入口,往里填麦个儿,一个紧随其后,负责传送。二伯常打前阵,累时再由四叔替换他。与大铁家伙近距离接触,比较危险,但并没有多高技术含量,只要动作麻溜,往入口处填麦个的速度能与快速旋转的机轮相匹配就好。多年干这活计,二伯轻车熟路,别人站在机器前不放心,总是亲力亲为。一双大手把解开的麦个放在打麦机入口,“嗡”的一声,机轮凭着惯性急速将麦个子吃进去,随即,出口处“哗哗”流淌出脱净的麦粒。这当口,二伯早已快速抽开双手,接过了另一捆麦个儿。
他们全副武装,戴着日本兵样儿的帽子,只留下一双黑色的眼睛。隆隆的机器声响彻夜空,木柱上挑起的夜灯,朗照这群挑灯夜战的人们。几十年后,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子里兀然涌出辛词《破阵子》首两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谁说麦场不是战场呢?是与飓风疾雨对抗,是在龙口里夺食!只可惜,它的热闹随着土地入户就消散而去了,成为永远的云烟。
打麦机凭着两张大嘴,一吞一吐,迅雷不及掩耳。小麦的植株在它体内纠缠搅动,被迫屈服,只留下胭脂色肌肤的麦粒,赤裸裸自出口涌出,不可计数,堆出小麦之丘。
麦场上最快乐的还是孩伢们,追逐打闹,抑或躲在阴暗处藏猫猫儿,笑声淹没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机器旁断不能靠近,电线纵横,机器中会有杂物飞出,大人早有禁令。谁要是不小心靠近,就会听到二伯盖过机声的吼,“一边子去,不要命了!”机器轰鸣声渐小,戛然安静,夜空一下子沉寂如水。人和机器需要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除下帽子、口罩,畅快地呼吸。灯光下,二伯和四叔眼睛旁一圈黑灰,鼻子下边也是。摘下手套,一双黑手伸在夜空,那形象,活脱脱两只黑猩猩。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稍稍靠近一些。看着外围的孩伢们,二伯做着鬼脸,扮猩猩的样子,张牙舞爪,故意吓唬我们。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顺势仰面躺在夜空之下。继而,又是严肃的一声:“小丫头,赶快回家睡觉去,明儿起不来炕,上学晚了,小心罚站。”我们一溜小跑,上桥,下桥,把笑声洒落在星辉斑斓里。
三
东小街真正以一条街来命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和话语中,是从麦地和谷地消失之时开始的。土地归属到个人,人们劳动热情空前。手里有了余粮余钱,便有了建造新居这一美好愿望。红砖瓦房一年年次第而起,如春雨后的麦田。我家、二伯、老叔、四叔、五叔,相继从旧居中搬出来,东小街成了我们家族的聚居地。
小街上立起的每一处瓦房都有二伯的心力。那时,建筑队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乡下人的头脑里。人们盖房大多选在开春忙里偷闲之际,由精壮有力且有盖房经验的劳力组成小团队,投入到建房造家的宏图伟业中,与黑旧之屋告别,拥抱清净敞亮的新居,还要靠着新房娶妻生子。日子如新生般,这是庄稼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二伯,无疑是这份幸福的奠基者。
听!“兄弟爷们呀”,二伯亮堂堂的大嗓门;“嗨嗨哟嗨”,众人的应和声;“铆足了劲哟”,“使劲儿砸呀……”伴随一轮又一轮这样的唱和,力盛的小伙子把夯举到头顶,再使劲往下砸去,完成建房砸地基的一个小回合。地基,经过这样难以计数的回合,方能坚硬如石。号子声响在半空,砸碎在泥土里,泥土由松软变得坚实。二伯和其他人一样,赤裸上身,古铜色的后背随着夯的升空暴起青筋,憋足气的脸又红又紫。落地的过程有短暂的调息,铆足了劲,又把夯举过尖顶,完成新一轮的使命。
二伯在东小街给自己三个儿子盖起了新房,他和二妈就从旧宅搬了出来,旧宅归属了别家。
旧宅夹在二队的住户中、桥西边的土街里。我常常在天气晴好,斜晖笼罩街道时,从东小街上小桥,慢悠悠走在悠长的西街。鸡犬相闻,各家门口站着下地归来闲唠的农人。我遵从母命,去自留地采摘新鲜的蔬菜。去自留地,有旁的道儿可走,我常常是专门穿过二伯家的宅院。宽阔敞亮,杂物很少,有着生产队长家的富足。二伯蹲在灶前烧火,专注的神情司空见惯。初见时,我实在不敢与那个在桥边、在地里,以及盖房时的二伯等同起来。二妈一直病体恹恹,老气管炎,长年喘不过气来,疾病折磨得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家务活儿一点儿也干不了,二伯将自己锤炼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匆匆拔了几根葱,摘了黄瓜豆角,踏着暮色,一路小跑,妈早等得不耐烦,正在门口候着。
二妈在东小街没住几年,困扰她大半生的气管炎带走了她的生命。在那个冷风呼号的凄寂冬夜,二妈在土炕头上闭着眼,艰难吐着气,气息微弱,如游丝,直至游丝尽无。她一直紧锁的眉头倏然展开。屋内一片号啕声。她其实不想走,敞亮的新房,三个儿子都已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孙儿绕膝,她还没享受够一声声脆甜甜呼唤“奶奶”的喜悦。
四
没了二妈,二伯的孤单在人们目光里。土炕偌大,只有他一个铺盖卷儿。二伯走在街上,他的佝偻之态更明显。他的右腿还有些瘸,年轻时落下了类风湿,右脚走路时往外撇着,像鸭蹼。他内心的孤单谁也无从体会。
二伯终究是二伯,他很快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过起了没有二妈的老年生活。他不再是当初那个一呼百应的生产队长,只是东小街一位极普通的庄稼汉,而他又不普通,他不靠儿女,一把年纪,日子依然过得滋润,如同蜜糖。
他在小桥西边路口摆上肉案,干起卖猪肉的营生。肥猪是二伯下到附近村儿收购来的'。“各家各户,有肥猪的卖喽!”喊声不减当年风采,一声又一声,响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通常在凌晨,村庄还在沉睡中,二伯家就会传来肥猪凄厉的叫声,二伯杀猪很准,一刀毙命,血哗哗放到搪瓷盆里。院子里架着硕大的锅,热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把猪抬到里面,洗去尘灰,褪去猪毛。猪耳、猪蹄不易褪净的地方,二伯专注且小心地用小刀刮净,之后,在猪腿上割开一个小口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不一会儿,猪身子滚成一个圆。二伯在儿子帮衬下,把白花花的猪挂在栋梁上,开肠破肚。刀锋过处,一股股血腥气飘出院子,弥散到东小街。
早上六、七点钟,二伯已在案前站定。腰间围着油花花的围裙,手上沾满油渍和血渍。案上,新鲜的两扇肉;猪头、下水、猪蹄、猪耳,都摆放在左手边。村里的、路过的外村人,都爱在他这里买肉。二伯不卖隔夜肉,不给小份量,要哪儿给哪儿。“来一斤五花肉,割回去大葱烙肉饼。”“好勒,您瞧好!”二伯的油手在围裙边上抹一把,尖刀在磨石上蹭两下,瞅准买主要的地方,刷,刀叫一个快,一条肉齐整整拎在二伯手上。系上麻绳,钩在秤上,“一斤,您瞧秤杆,高高撅着头呢……”
没人光顾时,他会坐到小桥石板上,从耳背取下提前卷好的香烟卷儿,在烟圈里沉思。沉思的时候,他看着这座石桥,早已不是先前模样了——人来人往,桥面凹凸不平,石块也缺棱少角。在桥下的波光中,他看到了自己强壮时的风光,想到了二妈走后一个人的孤独。人和桥都在时光中老了,桥下,流水越来越浅,岸也越来越宽。
没到晌午,肉案就只见血渍不见肉了。也有卖剩下的血脖,他拎回家去给几个孙子解解馋。
下午没事,二伯常去小街东头耍钱(赌钱)。堂哥堂姐劝二伯多少次也不管用。他理直气壮,“我自个儿挣钱,花你们一分一厘了?输了赢了不用你们管。”三个儿子拿他也没啥办法,也知道他输不了大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老有所乐吧。
摆了几年肉案,二伯钱包鼓鼓的。然而,那只像鸭蹼样的右脚逼迫他不得不摞下这个营生,何况,一年又一年的老态也让他不能长时间站立。终究是闲不得。炎夏来了,他又给自己找了个相对省力的营生,骑着自行车,车后卡着冰棍箱,到田间地头吆喝着卖冰棍。毕竟已近古稀,与当年砸夯时喊号子的嗓门相比,还是少了些底气。“兄弟爷们呀,来吃冰棍哟!”谁个不买,他就在地头儿不停使劲吆喝,直到把他们的馋虫子逗上来才罢。
“卖冰棍儿喽”,当这声音响在桥上时,小街的娃儿们像小雀般围住了二伯。二伯如往常一样,揭去棉被,小心取出将化未化的冰棍,分给吵嚷的娃儿们吃,喃喃的碎语间,竟有老婆婆般的温柔与慈爱。“不急,不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看着娃们抹着汗,伸着小馋嘴贪婪吮吸的模样,他掏出旱烟,坐在小桥的石板上,沉醉在吞云吐雾里,遐思由近及远。
衰老一直无情地追随他,摧毁他,他的病腿,他的日益弯驼的背。终于有一天,他拄着木棍,蹒跚上桥,蹲在他曾经卖肉的墙根儿下,成为了晒太阳的一员,游离的目光随着南来北往的人移动。孤独,如同一条绳索,紧紧捆绑着那个不愿屈服的躯体。更多时候,他的目光在桥上逡巡,桥和他一样,已经不堪重负,破损样子更让他心疼。能倒退几十年多好呀,他还有能力去修护一座桥,然而此刻,他只能把目光从桥上移到已经干涸的小河,移到河道上空,似乎,在那里才可以重温他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就像回潮般日日退却,只能轮流住到三个儿子家。那年春节我去看他,土炕局促,只有他一个铺盖卷儿的位置,然后就是码得直抵屋顶的土豆种袋子。这些土豆,在暖屋内生芽,春暖时,切块栽种到地里。二伯坐在炕沿,脸上漾着久违的笑意,看着他,我脑子快速播放着关于他的电影,一幕又一幕,虽久如新。
在二妈去世后的第十年,二伯走了,无大病之痛。那些小病如蛀虫一样啮咬、蚕食、吞噬了他。也许,他太想念二妈了,不愿意再孤独下去,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与二妈相伴了。出殡那天,一进村,我就听到了哀凄的唢呐声,如泣如诉,叙说着故去老人和与之相关的村庄历史。平日里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村子中的许多人自发来到东小街,默默地为他送行。没有喧哗之声,每一个前来送别的人满脸肃穆,在送走二伯的同时,也在与自己曾经的一段旧日时光挥手告别。
二伯去世前几天,桥身南侧莫名坍塌了一块,我回村奔丧时,它已经用铁架支撑起来,桥面的新土上,印着人们杂沓的脚印。故乡小桥,神奇而又充满隐喻,它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送别了二伯,却把这个村庄的故事永远留在桥上,讲给从桥上经过的每一个人。
五
自爸妈来城里生活,我回村的次数少之又少。除了过年过节,恐怕,就是因亲人离世而奔丧。熟悉的老面孔越来越少,陌生的目光多之又多,我恍然成了外乡人。小桥犹在,经过大规模的加固修整,老旧之容已经焕发了新颜。斑驳损坏的石块顺势推到东边河沿上,取而代之的是几块光滑平整的石板。一座古老又新生的小桥,继续担当着村庄的见证者和书记员。桥南侧,干涸的河床像老人掉光牙齿的牙床,东侧河内垃圾堆得几乎与道路持平。桥北已经被填平,建成民居,那段河流被封存成历史,若干年后将踪迹皆无。可我,总是会把目光飞越,飞越在东小街的上空,飞越在村庄的上空,这时候,脑子里会涌动出清水泛波的时光,还有二伯催动马儿时响亮的鞭声……
相关文章
山城花信散文2023-06-09 07:33:11
清明,追思公公散文2023-06-06 12:27:16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散文2023-06-13 02:49:55
相下有心,人思于尔散文2023-06-13 01:09:40
承认错误,才有进步散文2023-06-16 17:35:00
大学生活之随想录散文2023-06-10 21:30:4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对比哪个好(排名分数线区2024-03-31 16:25:18
河北高考排名237950名物理能上什么大学(能报哪些学校)2024-03-31 16:19:2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山东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5:16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2:5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09:19
安徽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招生人数和最低分2024-03-31 16:04:52
醉翁亭记主旨句2023-06-17 14:25:36
醉翁亭记读后感(四篇)2023-06-05 01:46:10
醉翁亭记教案范文集合十篇2023-06-19 05: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