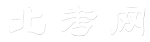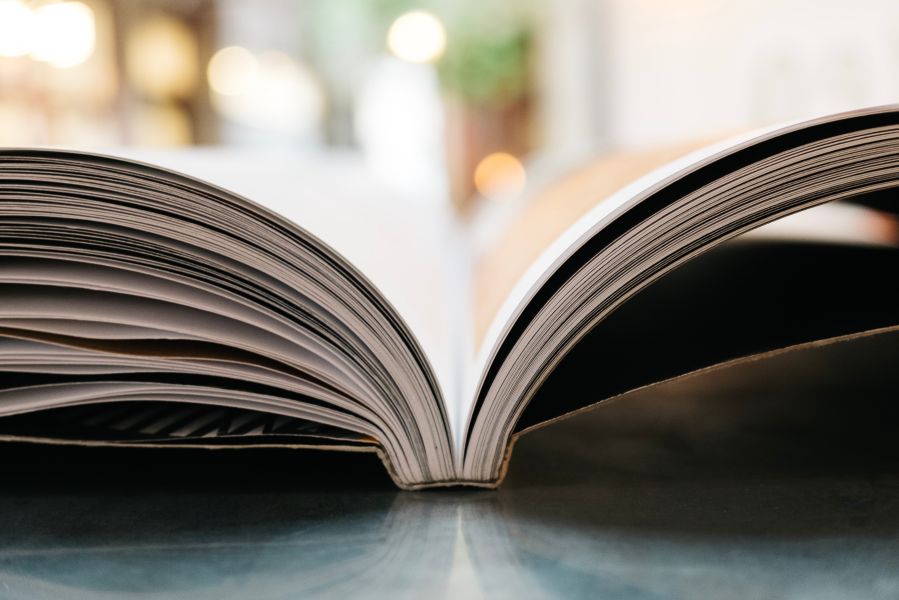鲁迅《在酒楼上》读后感
《在酒楼上》从叙述形式上观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人物“我”在讲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见、闻中,引出吕纬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事的叙述方位,但是,吕纬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见”只限于引出吕纬甫和介绍吕纬甫的肖像神态,吕纬甫登场后,即以第一人称主角人物的叙述方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吕纬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物“我”只充当一个听众。这样,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篇小说阐释中必须讨论的问题。
当吕纬甫以人物“我”的方位叙述时,又引进过另一位叙述者的叙述——老发奶奶叙述顺姑之死,这段叙述也是直接引语。从叙述形式看,这篇小说包括了主叙述、次叙述和次次叙述三个层次的叙述。主叙述:第一人称“我——在S城一石居酒楼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吕纬甫。次叙述:吕纬甫向人物“我”讲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次次叙述:老发奶奶向吕纬甫讲述顺姑之死。
《在酒楼上》的不同层次的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研究老发奶奶的叙述。老发奶奶是顺姑的邻居,顺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当然常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但是,在小说中,从老发奶奶的叙述看,有些内容并不是亲身的见、闻而来,比如“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整夜的哭”、“忍不住”显然已经超越了老发奶奶见闻的权力范围,是一种全知视角了。再如“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这一段,也没有权力自限。在是否有权力自限这一点上,老发奶奶的叙述与吕纬甫和人物“我”的叙述都不同,老发奶奶只是充当了一个交待顺姑结局并加以评论的说书人。老发奶奶的全知特权,正是吕纬甫叙述的权力自限的补充。没有老发奶奶的无所不知,这个外在于吕纬甫经验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结,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替作者设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结顺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个老发奶奶,完全可以让已经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顺姑的弟弟)或详或略地或感伤或木然地向吕纬甫叙述,为什么别生枝节地引出老发奶奶这个叙事者?如果考虑到吕纬甫叙述的基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吕纬甫挂在口边上的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他的叙述语调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吧。”这样,顺姑的悲剧性的死在叙述出来时就必须“扯淡”,年轻的又是亲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叙述者,老发奶奶恰是合适的。“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这是老发奶奶的评论与慨叹,可谓将顺姑之死的悲剧性扯得淡之又淡。将这一具体的人生悲剧纳入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陈腐公式,乃是将触目惊心的生离死别化作街谈巷议的一叹,在语调上与吕纬甫的叙述保持了一致性。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第二个功能。顺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长庚的诳语,但是相比之下,以当时S城的医疗水平而论,顺姑既已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无异宣判了死刑,长庚的诳语,对顺姑之死并没有直接影响,顺姑之死,真如老发奶奶所说,“这也不能去怪谁”,生了这样的病,死了,在老发奶奶们的观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点婉惜——“没有福气”。但是老发奶奶淡然的主观叙述中实际包含着顺姑的悲剧,一个现代读者自会在老发奶奶的叙述中,自然地读出。这是因为顺姑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姑娘,不仅美丽、善良、诚挚,而且能干(这在吕纬甫吃荞麦粉的叙述中已有交代),又有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带着以为自己的男人还“比不上一个偷鸡贼”的心灵创伤死去。这一悲剧性一旦与吕纬甫送花的意向相联系,就具有了对吕纬甫产生影响的力量。这实质上的悲剧性与老发奶奶“扯淡”的叙述构成一种反讽,实际上是吕纬甫心理张力的动力之一(此点在下文分析)。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三。从时间关系上说,老发奶奶的叙述,发生在吕纬甫到一石居喝酒之前,从空间关系说,发生在顺姑家斜对门,通过吕纬甫的口将老发奶奶的话转述,避免了地点的分散,保证了小说形式上的集中;而吕纬甫的叙述,是对自己十年以来在不同时空的人生经验的追述,这就保证了小说整体上的对于三一律的遵循。
现在研究吕纬甫的叙述。有一种倾向,即在分析吕纬甫时,根据吕纬甫自己的言语论定其形象及意义。比如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这样写道:
吕纬甫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既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屯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像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这样,吕纬甫也就是一个辛亥革命后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了。
上述对吕纬甫形象的分析,为一般文学史采用,这种结论,是建立在吕纬甫对自己的评价的基础上的,这从王瑶的论文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来。在《谈(〈呐喊〉与〈彷徨〉》中,作者写道:
……他本来是个很敏捷精悍的人,青年时候为了破除迷信,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辛亥革命以后,他经过多年地辗转流离,生活的打击,意志便慢慢地消沉下来。青年时代的理想消灭了,现在生活里一点目标也没有,只是“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他原来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竟教起“子曰诗云”之类的封建的东西。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只能做些无聊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不满,但又无力自拔,鲁迅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生活,像苍蝇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种苍蝇似的悲剧。小说里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吕纬甫给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葬;一个是他给一个叫阿顺的女孩子送去两朵剪绒花。这两个细节选择得非常精当,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他都做了,深刻地表现了他只做了些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那种空虚的精神世界。鲁迅写他们在酒楼上喝酒的情景非常凄凉。作者对吕纬甫的态度有同情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小说的结尾写他们一同走出店门,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各自走去了。这是一种批判。
这样的分析,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中,是很精细并且也比较贴近作品现实的,但是,由于在分析方法上,未能注意到叙事形式,不能不有一种先天局限。
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吕纬甫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取了主角叙事的角度。他所叙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从真实性的角度看,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事实,一是对于事实的主观态度。这个主观的态度,是一种自我评价。人物的自我评价,是自大自狂式的,还是自卑自贱式的,亦或是公允平和的,是分析中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本文第二部分也已经指出,作为人物的回忆者我的叙述成立的前提是作为经验的我的存在,先有日后的观照者之我对于感知者、经历者之我的审视观照,而观照的前提正是回忆,由此可以整理出作回忆叙述之予的精神活动的第一层次:
感知者、经历者之我//回忆者之我
在这一层次,毫无疑问,有一少一多,一少是指“感知者、经历者之我”的事件不可能全部被回忆,得到记忆并能够回忆的总是对于主体有意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是主体觉得值得回忆的东西,因此,我们说,感知者、经历者之我”是历史的、事实的,被回忆的我则是价值的、意义的。从研究讲,我们固然可以透过回忆追溯历史的、事实的我并进而作出对于历史的事实事件的判断与评论,然而更重要的也常常被评论者忽略的是对于回忆之我之价值的意义的世界作深入的解读。这一与回忆之我相联的价值、意义就是一多之多,它们是原本的事件中没有的。
况且,吕纬甫的自述,概括了近十年的人生历程,从底本与述本的关系看,十年的故事进入述本的微乎其微,则述本中的这个“微乎其微”的故事被叙述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吕纬甫的叙述,实际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考察这一言语行为,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为什么要提出语境?乃是因为言语的意义往往并非存在于言语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与语境的特定关系之中,离开语境,其意义便无可索解。举例来说:“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摆。”和“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拿。”这两句话,与“你放着果,祥林嫂!”都是很平常的话,在小说中是祥林嫂性格与命运转折的关键,但这种意义单从语言结构本身分析是茫然无绪的,必须将这些结构简单的言语与祥林嫂的捐门槛,与鲁四老爷家的祭祖以及鲁四老爷讲理学的环境联系起来,才能比较准确理解这些言语的意义。同理,吕纬甫的叙述,乃是面对人物“我”的一次谈话,离开这个基本的语境,仅就其言语本身,是不能全面理解他的言语行为的。在小说中,构成吕纬甫言语行为语境的,有下列因素:①吕纬甫进入一石居之前的事件——老发奶奶的叙述,②一石居酒楼的自然环境,③吕纬甫的对谈者人物“我”,由于十年前的人物“我”——即吕纬甫所知道的人物“我”——是一个“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的友人,因此,人物“我”的对坐,意味着吕纬甫面对十年前的“旧我”,面对自己十年来的人生历史。正是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人生志向与实际人生实践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吕纬甫叙述的内在反讽关系。这种由于语境决定的反讽关系制导着吕纬甫对于底本故事的择取,规定了吕纬甫对于自己的评价。如果把吕纬甫的自我估价视为作者权威的评价,忽略吕纬甫叙述中的矛盾,小说的分析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简单化的框框。历来的研究家都承认并推崇鲁迅是一位文体家,如果这些各别的文体无关乎小说的意义阐释,则不啻说鲁迅是一位玩弄形式的形式主义者。
根据上文所述,评价分析吕纬甫的三个着眼点——主观的自我估价、叙述加工和语境,现考察吕纬甫的形象及意义。由于语境具有根本的意义,故从语境分析入手。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处于论争状态”,所谓论争状态,我以为就是叙述者面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自诉、自评和自我辩护,不独吕纬甫如此。
当吕纬甫到一石居之前,正是送剪绒花的时候,送花之前,是迁葬。这两件事可以说都是有意义而又无意义的,这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看,就其与社会的关系看,可以说是无与于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是无意义的,从社会进步的功利观出发,甚至可以说是无聊的。吕纬甫每每称这类事为“无聊”,也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这类事,即使做了,也“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在这个层次上,“无聊”一词,说明叙事者的衡量事物的标准、批评事物的价值尺度是十年前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这一方面,吕纬甫似乎还很执著。吕纬甫所以采取这样的批评标准来作自我否定,正是对话语境的特定反应。人物“我”对于吕纬甫,意味着十年前理想、理念的重视,意味着“旧我”的记忆唤醒。在面对十年前之“旧我”时,是据现在之人物“我”以笑谑少年的孟浪幼稚,亦或是感慨唏嘘,将种种矛盾付之一叹?看来都不是。吕纬甫仍然用十年前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在衡量之中,暴露出巨大的差异与矛盾。这一矛盾是留给叙述接受者人物“我”的。其实也就是对于理想的诘难,对于旧我的诘难。故而本质上乃是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的论争关系的表现。
送花与迁葬的叙述并不如此单纯,对于叙述者吕纬甫而言,并非全无意义。迁葬、送花在一面,固然是为了母亲的心愿,但是,吕纬甫也是愿意的,就因为这都与他的情感的`丝缕相牵系。在人伦关系中的小兄弟,是据说与他很相投的,但是掘开这使她母亲牵记而着急的坟墓时,叙事者说:
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竭力要寻出点牵记着情感的那些实有的事物,结果是“踪影全无”——这是以有意义始,以意义的消解终——真正是“无聊”,这个“无聊”,是对于自己而言的无聊。“送花”同“迁葬”的差别不是很大,既是为母亲,也是为自己,为了自己曾经受到过顺姑真挚而热情的“款待”,所以,吕纬甫竟然非常认真、非常勤快,并且格外地周到,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但是,顺姑死了。与吕纬甫过去相联系的一些人事,因这些人事而生的情感的牵累,竟也是虚空之至。“送花”这一事件,在时间上,与人物“我”在S城寻访旧友差不多,且看人物“我”之叙述:
…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竞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城固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人物“我”的访友与吕纬甫的送花性质乃是一样的,是一种类似关系。他们都因情感的牵累而来,结果都得到虚空,都感到无聊,并且都想到了“一石居”。人物“我”的进“一石居”,“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吕纬甫应该也不例外。吕纬甫向人物“我”叙述其“无聊”乃是诉说人生之百无聊赖:于社会,早已无与于进步文明,于个人,连情感的牵系也抓不住、摸不着,那么,人活着的依据是什么?这是吕纬甫叙述的另一意向,是特定语境中对于听者的发问,也是自问。但是这一叙述与人物“我”的叙述是一个类似关系,其实也是人物“我”所不能、无法解答的问题,故而这两者的叙述构成一个潜在的反讽。
吕纬甫其实还应该可以与鲁迅的另一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合观。在曾为之奋斗的理想落空后,二者都是在情感的牵系中寻找生活的依据,一为爱,一为恨,但倘若认真地思量,爱也虚空、恨也虚空,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所不同者,吕纬甫的老母亲还没有死,所以他还必须活着,必须去做那些他未必想做的事,魏连殳的唯一的亲人老祖母一死,他便任心而活,结果于人无损,倒是毁了自家。古代也好、近代或现代也罢,从理论上说,从社会实际人生样态说,人的活法其多也不可胜数,但吕纬甫的叙述中,始终要寻找的是人生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又总是以他人、以社会为条件的,这或许竟是革命浪潮中被唤醒的纯洁而又平庸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特征。革命浪潮带给他们价值观念,带给他们理想,但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就夭折了,历史不会重来一遍,革命即便再次发生也早已换了花样,不再是这套把戏,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为自身准备的那些虔诚的香客信徒,要么改弦更张,要么作那革命的无谓的殉葬品——那样的革命永远不会再来。我们也许可以说,吕纬甫乃是“革命遗少”的符号。
吕纬甫的话语也就成为对于人生意义的两个方面的质询:对外与对内,外面人生的价值与内面人生价值同时落空,则他的教“子曰诗云”甚至《女儿经》以谋生也就无所谓,这正是对今天之人物“我”的辩护——反正无意义,干什么都一样:“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从以上解析可知,离开话语语境,或者说不考虑吕纬甫自叙的形式,仅从其自叙中拣取一、二片断是不足以论析人物的。
另外,还应该注意,吕纬甫的叙述是一种贬低陈述,他总是说得轻松:十年的人生经验代之以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事小事,一律调之“无聊”,总之是挑那些最无足轻重者说,这是有意的自我贬抑,与这种自我贬抑相对应,是对人物“我”的期待:“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在论争性的语境中,人物“我”并非一个被动的听众。当人物“我”为逃避“无聊”进入一石居之前,其心绪与进入一石居的吕纬甫颇为相似。人物“我”所以绕道到S城,原是为了重游故地、重会旧友,结果发现一切(包括学校)“于我很生疏”,发现人物“我”成了故乡的“生客”,“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这件事如果让吕纬甫来叙述,就是“无聊”。而“无聊”竟可以说不仅于此——“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差不多也是十年来的概括,故而“我’有哀愁。这一心态正是人物“我”乍见吕纬甫时有点自卑而惴惴的原因。“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过去,十年前,他们是改革中国的理想下结成的朋友,现在,人物“我”记忆中的他仍是十年前的他,而担心不配作其朋友,但心他不肯以自己为友,则人物“我”也早已无与于社会改革进步的事业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人物“我”见到吕纬甫之后,即开始了对于友人的观察、探寻。“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迁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这是人物“我”的一看,这一看是将当前的与十年前的友人作了一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变了,也变了。但这一比较尚不明确,所以有二次的细看:“细看他的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这二看,是进一步的比较、探寻,其结果,却又似乎是尚有不变者在。在对方尚有“学校时代”“射人的光”的发现下,人物“我”是不自在的,“不自然”的。等到互相通报近况之后,吕纬甫以苍蝇绕圈子的比喻为二人作了概括。接着,是吕纬甫对于人物“我”的询问:“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这是询问,也是期望。而“我”也对吕纬甫有所期望——“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于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说到底,两人的心态是相同的,在十年之后相对时,十年前的友人成了各自观照自身观察对方的镜子,也即等于各各将友人推到十年前立下的理想前,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作出评判与解说。换言之,两个人物相对时,其对话关系实质上是相互形成压力,迫使各自对十年前的理想作一交代,对现在之我作一辩护,这就是二叙述者叙述之中的论争性关系。
而小说中的二个“我”的关系, 又未尝不是鲁迅自己精神世界矛盾的一种表现?简短的结论。
相关文章
我的偶像鲁迅作文600字(精选10篇)2023-06-04 02:42:42
关于鲁迅教案2023-06-18 03:19:13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文学和出汗2023-06-16 05:13:21
鲁迅故乡的叙事艺术特点2023-06-02 08:11:23
有关鲁迅的经典名言大全2023-06-09 20:30:05
鲁迅作品谈金圣叹2023-06-09 00:01:5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对比哪个好(排名分数线区2024-03-31 16:25:18
河北高考排名237950名物理能上什么大学(能报哪些学校)2024-03-31 16:19:2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山东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5:16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2:5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09:19
安徽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招生人数和最低分2024-03-31 16:04:52
醉翁亭记主旨句2023-06-17 14:25:36
醉翁亭记读后感(四篇)2023-06-05 01:46:10
醉翁亭记教案范文集合十篇2023-06-19 05: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