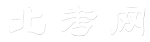郭沫若《漂流三部曲》赏读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羼走。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圣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钟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诿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什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什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痈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什么?少我一个又有什么?”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什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
他女人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他说:“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
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没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但是终竟苦干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
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装,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起程时,街灯还未熄灭,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车到黄浦滩的时候,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又要登上它的征程了。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
——“那些轮船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有些是到外国去的。”
——“哦,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到日本去的船在哪儿呢?”
——“还远呢,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
他同他的大儿对话着,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儿,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在那海边上呢。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
——“唔,拣金蚌壳儿呢,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
他一路同他儿子们打着话,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是的,在船上去补票罢。……”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什么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他决下心不去了,但又悬想到路上的艰难,又决心要去。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斡。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默默不作声息。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但不久也就象在摇篮里一样,安然地在他母怀中睡熟了。
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车到汇山码头了。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尾舶上现出白色的“长崎丸”三字。码头上还十分悄静,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了之后,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孩子们快乐极了,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最小的婴儿却好象和他惜别的一样,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声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时,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
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好象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这回回去,无论如何是应该雇用女工才行。十块钱一个月总还可以雇到罢?”
——“总可以雇到罢。”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听说自从地震以后,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但是福冈又不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他这么说了一半,但他在内心中早狐疑起来了。找钱?钱却怎么找呢?还是做文卖稿?还是挂牌行医?还是投入上海Zigoma团①去当强盗呢?……
①作者原注: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
——“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个儿子,怎么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总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长过颈子来,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他和孩子们也一一接吻过了,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见人,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是起来迟了?还是改了期呢?动身的时候,悔不曾去约他。他跑出舱来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他一方面望T君快来,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走出舱来,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有的脱帽招摆,有的用白色手中在空中摇转。远远望去,一乘马车,刚好到了码头门口。啊,好了!好了!T君来了!车上下来的果然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船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我怎么样呢?还是补票吗?还是上岸去呢?”他还在迟疑,他女人最后对他说:“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停了几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心机也好。”
他女人的这些话头,突如其来,好象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又响彻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①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②永远的女性哟!……”他决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别,拜托了一切之后,便毅然走出舱来。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来,免惹得孩子们流泪。
①作者原注:但丁。
②作者原注:“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上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
几声汽笛之后,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做‘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Ava Maria,Ava Maria……永远的女性!……Beatrice……‘洁光’……”他直到走上了电车,还隐隐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黄浦江里去。
长期的电车把他心中的激越渐渐缓和,给予他以多少回想的余暇了,他想到他历年来的飘泊生涯,他也想到他历年来的文学成绩。“啊,我的生活意识是太暖昧了。理想的不能实行,实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混过了大好的光阴。我这十年来,究竟成就了些什么呢?医学是不用说了。虽然随着一时的冲动做过些诗文,但那是什么东西哟!自己的技能有哪一样能够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哪一篇能够足以自我安慰呢?啊,惭愧!惭愧!真是惭愧!我比得什么Dante!我比得什么Dante!我是太夸诞了!太无耻了!啊,我是……”他这么想着,又好象从灿烂的土星天坠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成了他莫大的重担。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卫的微石①了。他的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的得不堪,假使电车里没有人,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
①作者原注:《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每含西山木石填东海,一名冤禽。”《博物志》:“炎帝女溺死,化精卫,与海燕为偶。生子雌曰精卫,一名冤禽,雄曰海燕。”。
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本来是他几年来的深刻的经验。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见烦躁,愈见烦躁,他愈见自卑。直到现在,他几乎连笔也不能动了。“自己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一知半解的评论,媒婆根性的翻译,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同情我的人虽说我有‘天才’,痛骂我的人虽也骂我是‘天才’,但是我有什么天才在哪儿呢、我真愧死!我真愧死!我还无廉无耻地自表孤高,啊,如今连我自己的爱妻,连我自己的爱儿也不能供养,要让他们自己去寻生活去了,啊啊,我还有什么颜面自欺欺人,忝居在这人世上呢?丑哟!丑哟!庸人的奇丑,庸人的悲哀哟!……”他想起John Davidson的一首诗来。诗中叙述一位贫苦的音乐家,因为饥寒的缘故把他最爱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头的他妻子的残骸,悲痛地号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My wofk,this woman,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there is no God.
这节的意思是:
我们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养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这个儿,
都已没了:谁说有什么天主。
他应着电车的节拍,默念起这节诗,他觉得好象是从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样。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没有这音乐家的真挚。音乐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纪念而世人湮没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什么资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儿是由自己抛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乐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残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极终竟随他的妻儿长逝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妻子向东,他自向西,妻子在漂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这儿梦想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攫吗?他一想到这儿,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儿回去。“我为什么不在船上补票?我为什么不去和他们同样受苦呢,啊,我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这责任观念薄弱的小人!……”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他就好象埋没在坟墓里一样。他没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象一座死城,好象有什么比死还厉害的东西在埋伏着的光景。他掉头跑出弄子来,跑到这静安寺路旁的街树下羼民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视着前面,街面上接连的汽车咆哮声都不曾惊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沧洲别墅转角处便伫立住了,凝视着街心的路标灯不动,这是他的儿子们平时散步到这儿来最爱留心注视的。他立了一会,无意识地穿过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来。走到圣智大学附近,他又蓦然伫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时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两个大的孩子散步到这儿来,一只瓦雀突然从洋梧桐上跌下,两个孩子争前逐捕,瓦雀终竟被他们捉着了。他那时曾经做过一首诗,此时又盘旋上了他的脑际:
橙黄的新月如钩,已在天心孤照,
手携着我两稚子在街树之下逍遥;
虽时有凉风苏人,热意犹未退尽,
远从人家墙上,露出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只蓦地从树枝蹴坠,
两儿欣欣前进,张着两只小手追随。
小鸟曳立悲声,扑扑地在地面飞遁,
使我心中的弦索也隐隐咽起哀鸣:
娇小的儿们呀,这正是我们的征象,
我们是失却了巢穴,漂泊在这异乡,
这冷酷的人寰,终不是我们的住所,
为逃避人们的弓弹,该往哪儿去躲?
无知的儿们尚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是欣欣含笑,追着小鸟飞驰。
我也可暂时忘机,学学我的儿子,
不息的鸣蝉哟,为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树讴吟了一会,念起昔日清贫的团圆远胜过今日凄切的孤单,他的眼泪如象喷泉一样忍勒不住倾泻下来了。在这时候,他真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零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象对他含着敌意,京沪的报章上许多攻击他的文章,许多批评家对于他所下的苛刻的言论,都一时潮涌了上来。一种亲密的微笑从面前飞过的一乘汽车的轮下露出,暴尸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来,肠爆了出来,眼睛突露了出来,脑浆迸裂了出来,这倒痛快,这倒痛快。“那时候尽一些幸灾乐祸的人们来看热闹,我可以长睡而不恼。……但是妻子们的悲哀是怎么样呢?朋友们的失望是怎么样呢?她怕我受累赘,才带着儿子们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长篇呢。每周的杂志,也好象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要待我做文章呢。这是我死的时候吗?啊:太sentimental①了!太sentimental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这死尸中从新赋与了一段生命。我这几年来并不是白无意义地过活了的。我这个生命的炸弹,不是这时候便可以无意义地爆发的。啊,妻儿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我回去,回去,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洁光’表现了出来。……”
①作者原注:伤感。
他的脚步徐徐移动起来了。他如何抱着旧式结婚的痛苦才跑到东洋,如何自暴自弃,如何得和他的女人发生恋爱,如何受她的激励,……过往十年的回想把他运回了寓所。客堂里的挂钟已经一点过了。一位老娘姨问他吃饭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楼去。但把房门推开,空洞的楼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气。他噤了一下,走向房里的中央处静立着了。触目都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两张棕网床,一张是空无所有,一张还留下他盖用的几条棉被。他立了一会,好象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张靠书台的藤椅上。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还是只好借笔墨来攻破了。他把书台的抽屉抽开来,却才拿出了他儿子们看残了的几页儿童画报,又拿出了一个两脚都没有了的洋囝囝。在这些东西上他感觉着无限的珍惜情意来。他起来打开了一只柳条箱子,里面又发现了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国的棉衣,他低下头去抱着衣裳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一种轻微的香泽使他感受着一种肉体上的隐痛。他把洋囝囝和画报收藏在箱子里面了,又回到桌边,才展开一帖原稿纸来,蘸着笔在纸端写下了“洁光”两个字。——他的笔停住了。怎么样开始呢?还是用史学的笔法从年月起头呢?还是用戏剧的作法先写背景呢?还是追述,还是直叙呢?还是一元描写,还是多元呢?还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十年的生活从什么地方起头?……他的脑筋一时又混乱起来了。他把夹着笔的手来擎着右鬓,侧着头冥想了一会,但仍得不出什么头绪。一夜不曾睡觉的脑筋,为种种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乱了的脑筋,就好象一座荒寺里的石灯一样,再也闪不出些儿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兴奋,他听着邻舍人的脚步声就好象他自己的女人上楼,他听着别处的小儿啼哭声,就好象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儿们呢?怕已经过了黄海了。“啊,他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我只希望他们明天安抵福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生出什么意外。”他一面默祷着,一面把笔掷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脑筋简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脱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纳头便倒在一张床上睡去。……马蹄的得得声,汽笛声,轮船起碇声,……好象还在耳里。抱着耶稣的圣母,抱着破瓶的幼妇,黄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eatrise,棉布衣裳,洁光,洁光,洁光,……
凄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楼房,两日来疲倦了的一个精神已渐渐失却了它的作用了。
1924年2月17日
①作者原注:外文为Purgatory。基督教的说法:不完全的信徒,在进入天国之前,要先在地狱里锻炼灵魂,洗涤生前罪愆。这地狱就叫做“炼狱”。但丁的《神曲》,诗人魂游三界,其第二界即为“炼狱”。这篇的用意略取于此。
爱牟自从和他的夫人离别了,半月以来时常和孤寂作战。但他作战一次,失败一次,就好象不谙水性的人,船破落水,在自齿的水波中,愈见下沉,愈想奋发,愈想奋发,愈见下沉,结局是只有沉没在悲哀的绝底了。他的寓所本是一楼一底的民房。自从他夫人去后,一切陈设都足使他伤感。他在当晚便去邀了几位朋友来,一同住在前楼,把全家的布置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改不了的,终是他自己的身心。他隔不几时又深悔何不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索性沉没在悲寂的深渊,终日受泪泉的涤荡。他对着朋友们时,时常故意放大声音讲话,放大声音发笑,但在话未落脚,笑犹未了时,他又长叹了起来。这种强为欢笑的态度,于他实在是太不自然,并且是太为苛刻,他和朋友们同住没有两天便又一个人搬到后楼的亭子间里去了。
这座亭子间除一床一桌而外,只有四面墙壁。他一人蛰居在这里,时而讴吟,时而倒在床上伸长两脚一睡,觉得太无聊时也起来执执笔,想写东西,但是总写不出什么条理。他不知道几时早把他夫人留下的一件棉衣从箱子里取了出来放在床上,他睡的时候,总要把棉衣抱着亲吻一回;然后再把来贴身盖着。他的夫人有和女友们合照的一张相片,他把她剪了下来,花了两角钱,买了一个相匣,龛饰起来了。他倚案时,相匣是摆在桌上,睡时,又移在床头,偶尔一出门也把来揣在怀里。
——“晓芙!晓芙!你怎么不同我讲话?你现刻在做什么?儿子们又在做什么?”
他时常对着相匣这样说,他的两眼总是湿涔涔的。
无论你是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总是不会减少。他到近来索性自暴自弃起来了。时而赌气喝酒,时而拼命吸烟。朋友们问他何故如此,他说这便是自杀。但是等他酩酊过后,酒烟的余毒,良心的苛责,又来磨荡着他。他时时向着相匣请罪,屡说不再吸了,不再喝了,严烈的发誓已经发过了多少回,但他依然敌不过“悲寂”的驱遣。朋友们都很替他担心,有的劝戒他说:蓄意沉浸于悲哀是但丁所不许的;有的说:他是有家室的人,不能如法兰西士·汤姆孙一样在楼阁中拼一个饿死。这些亲切的友谊他也很能怀着谢意去接受,但他总是不能自拔。
“长此浸淫着实在是不成事体,妻儿们的生活费还全无着落呢,我索性离开这家屋子,或者索性离开上海罢。”他有一天中午和着衣裳就寝的时候,他的心里正在这样作想,后门的门铃响了,同住的尼特君替他拿了一卷邮件上来。他满以为是他夫人给他的信,但他接着看时,却是从无锡寄来的。他拆开一看,除去一些原稿之外还有一张信笺,他便先拿来读了。信里说梅园的梅花盛开,太湖上的风光已随阳春苏转,希望他和芳坞诸人同去游玩,也可以消除他们的愁烦。
“啊啊,这是和悲哀决斗的武器了,我索性暂时离开上海罢!”
他决绝地跳下床来,拿着信走到前楼来向芳坞说道:
——“无锡的嘉华和瘦苍邀我们去游太湖,你愿意去吗?我们礼拜去罢。”
——“唔,唔,礼拜去,礼拜定去。”芳坞回答了他,他又转向尼特:
——“尼特也去罢。”
——“去,你先写一封快信去就行了。”
他得了他们的赞成,随即写一封快信,约定后日乘早车到无锡。
第二天是礼拜六,他蛰居在家里仍和平常一样。晚上有人招饮,他也勉强出席了。席中有人问及他的夫人和儿子的,他触到伤感处,不禁又痛饮起来。一席的人他都和他们对酒,饮到席罢,他已经难以支持,东抱一人接吻一回,西抱一人接吻一回,同席的人他几几乎都接吻遍了。他的脑筋还有几分清醒,他一面在狂态百出,一面也在自己哀嘲:看你这个无聊人究竟要闹到怎样?你坐这儿享乐吗?你的妻子还在海外受苦呢!……酒的烈焰煎熬着他,分裂了的自我又在内心中作战,他终竟支持不住,在友人的家里竟至大吐了一场。芳坞把他送回家,他坐在人力车上一路只是忏悔,从衣袋中取出他夫人的相匣来冰在自己的的额上。
刚回家,他一倒在床上,便抱着他夫人的棉衣深深地睡去了。
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早亮了。心尖不住地狂跳,前脑非常沉重,而且隐隐作痛。他口渴得什么似的,几次想起床寻茶水喝,但都没有勇气。最后他终竟忍耐不住,推开棉被抬起半身来时,他才看见桌上正放着茶壶和茶杯,原来芳坞在他睡时已经给他预备好了。啊,友情的甘露!他接连呷了几杯,一股清凉的滋味一直透进他的心底。他想趁势起床,但头脑总是沉重得难耐,他又依然倒下去睡着。
——“爱牟,怎么样了?还不起来。”芳坞走进房来催他。
他说:“不行,我头痛,你和尼特两人去罢,我今天不能去了。”
——“起来哟,赶快,你起来便会好的。已经七点钟,赶七点三十分钟的车还来得及。”
芳坞说着便下楼去了,他在床上还迟疑了一会,结局还是坐了起来。不去觉得对不住朋友,便留在家中也还是一样受苦,他便决心起了床。但是,头总是昏腾腾地作痛,走起路来总觉得有点摇晃的意思。
七点三十分的车他们也赶不及了,便又改乘九点半钟的快车。上车的时候,三等车的人已经坐满,芳坞和尼特只在车外站着,爱牟一个人却去找到了一个座位来坐下了。他只呆呆地坐着,邻近的人都向他投视一瞥疑怪的眼光。他心里时常起着不平的抗议。车出上海以后,窗外一片荒凉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阳光里,他觉得这种风光就和他自己的心境一样。
车到苏州时,下车的人很多,芳坞和尼特才得走进车来。
——“爱牟,你怎么样了?脑子不痛了吗?”芳坞一进车来便关心着他。
——“已经不痛了,究竟还是来了的好。假使呆在家里,包管有两三天是不会舒服的。”
谈不两句话,爱牟又沉默着了。他看见尼特坐在车隅看书,芳坞贪看着车外的景物,心里很羡慕他们的自由,只他自己是在茧中牢束着的蚕蛹。灰色的苏州古城渐渐移到车后去了,爱牟随着车轮的声音低低地讴吟了起来,声音高的时候,听得的是“……吴山点点愁……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几句。
无锡的惠山远从荒茫中迎接前来,锡山上未完成的白塔依然还是四年前的光景。四年前爱牟本在惠山下住过。他因为生活的不安,在那年的四月,向学校告了半年的假离别了他的妻子,从日本跑回了上海。上海的烦嚣不宜于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象灼热的沙漠上折了翅膀的一只小鸟,他心中焦的得什么似的。一直到七月,因友人盛称惠山的风光,并因乡下生活的简易,他便决计迁来。起初原拟在山下静静地译述一两部著作,但是惠山的童裸,山下村落的秽杂,蚊蚋的猖狂,竟使他大失所望。他住不两天接到从上海转寄来的他夫人的信,说是因为房金欠了两个月,房主人迫着他们迁徙了。他拿着信,一个人走上头茅峰去,对着晓雾蒙蒙中的旭日,思念着他寄留在东海岛上的可怜的妻儿,他的眼泪流在脸上,知道他的苦痛的怕只有头茅峰上的石头。他那时终竟不能安定,便在当日又匆匆地折回了上海。
头茅峰上的石头已渐渐可以辨别了,新愁旧恨一时涌上心头,爱牟又苦到不能忍耐了,“啊啊,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是来寻乐的吗?现在是该我寻乐的时候吗?这儿是可以寻乐的地点吗?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想做的长篇不是还全未着手吗?啊,我这糊涂虫!……”他一面悔恨着,但不容情的火车已把他拖进了无锡车站。芳坞和尼特催着他下了车,他在月台上走着,打算就改乘同时到站的下行车,折回上海;迟迟疑疑地走到出口处时,嘉华和瘦苍两人又早捉着了他的两手了。
嘉华和瘦苍两人在车站上已经等了他们半天了,另外听说还有,一位朋友想私下见他们一面的,也同在车站上等着,他为友人们的浓情所激动,他的精神才渐渐苏活了转来,“啊,真丑!真丑!我简直没有骨头!”他们握着手一直走到繁华的市上,在一家饭馆里用了中饭,便同路绕道惠山,再向太湖出发。
童童的惠山,浅浅的惠山,好象睡着了几条獐子一样的惠山,一直把他们招引到了脚底。他们走过了运河了,一千四百年前隋炀帝的二百里锦帆空遗下一江昏水。“啊,荣华到了帝王的绝顶,又有什么?只可惜这昏昏的江水中还吞没了许多艺术家的心血呢!……你锡山上的白塔,你永远不能完成的白塔,你就那样也尽有残缺的美,你也莫用怨人的弃置了。……丛杂的祠堂和生人在山下争隙;这儿只合是死人的住所,但是在这茫茫天地之间,古今来又真有几个生人存在呢?……永流不涸的惠泉哟,你是哀怜人世的清泪,你是哀怜宇宙的清泪,我的影子落在你的眼中,我愿常在这样的泪泉里浸洗。……”
空气是很清新的,在冷冷的感触中已经含有几分温意。走向太湖的路上沿途多栽桑木,农人已在锯伐枝条,预备替绿女红男养织出游春的资料。迎面成群的学子欣欣归来,梅影湖光虽还保留在他们健康的颊上,但在他们匆匆的步武声中已在预告着明朝的课堂铃响了。只有幽闲拓大的水牛,间或有一二只放在空芜的草地上,带着个形而上学家的面孔,好象在嘲笑人生忙碌的光景。路虽宽广,但因小石面就,毕竟崎岖不平,爱牟右脚上的皮鞋,因在脚底正中早已穿破了一个窟窿,他走起路来总觉得脚心有些微痛。他跛蹇着跟在同人的后头,行路是很缓慢的。他们约摸走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将近要到茶巷了。瘦苍止住脚,叫嘉华引他们到东大池去,他到茶巷去寻人力车来再往太湖。
——“东大池?是什么名胜地吗?”爱牟忍不住向嘉华发问了。
——“这里有一家别墅,是我们去年替你找就的。去年我们几次写信给你,叫你来你总不来,现刻还空着呢。我们去看一看罢,你看了定会满意。”
去年爱牟回国的时候,本打算不住在上海,想在邻近的乡下卜居,以便从事著作并领略些江南风味。嘉华们听了,便邀他往无锡。但是无锡他是到过的地方,三年前失望的经验使他生了戒心,所以终竟没有放下决心。在再将近一年,无锡他不曾来,别处他也不曾去,蛰居在上海市中使他从前的计划归了泡影,连他自己的妻儿也不能不折回日本去了。这是他失败史中的一页,从此不能扯去的一页!
瘦苍走向茶巷去了,四人改途向北,折入田地中的一条支路上去。路直趋山麓,走不多远有小学校舍一间,校门都是严闭着的。转过校舍后现出一面溶溶的大池,池水碧绿而不能见底。池形如象倒打一个问号一样,在撇尾的一点处,一座大理石的洋亭,是两叠两进的结构。亭下有石槛临池,左右有月桥,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成林,树虽不古而幽雅成趣。三面环山,左右形如环抱。爱牟和芳坞尼特都惊异了起来。
——“啊,有这样好的地方!”
——“有这样好的地方!”
——“这简直是世外桃源了!”
冷静的嘉华引着他们只娓娓地细说:“这儿听说是前年才开辟出的,只有一个老人留守。我们在无锡住了五年,一直到了去年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同学们都不知道,有的只说是荒凉了一点,但我们来看时全无荒凉的感觉。我们满心以为你们会来,把交涉都办好了,只要你们一回信,便请校长作函介绍,立地便可以居住的,留守的老人也非常欢喜,他以为他可以不寂寞了。”
沿着池东一直走过月桥,便走到别墅的区域。沿途有新植的梅花,已经开放。爱牟一路吮吸着梅花的清芬,静聆着流泉的幽韵,他的一心好象起了几分出尘的逸想,而他的一心又涌上了无穷的懊丧。“去年为什么要辜负朋友的盛意终竟不肯来呢?我真是作孽自受!……”石亭后面是一面草场,草场尽处便是一列三间的住宅。住宅的'形状颇类庙字,屋浅无楼,结构本不甚美好,然而四方的风物也尽足补偿它的缺陷了。住宅右手还有一带翼房,留守的老人正在门前织履。
石亭拥立在假山石上。底层前为空阁,后为石窟。上层前为平台,后为亭屋。平台三面均有石栏。正中有圆形石案,有石凳环绕,登台一望,全池景色尽在眼中。风声鸟声,松声涧声,凝静之中,时流天籁。坐在这台上负暄,坐在这台上赏月,坐在这台上读书,坐在这台上作文,坐在这台上和爱人暖语,坐在这台上和幼子嬉戏,……这是多么可乐的情事哟!每当风清月朗之夜,清友来游,粗茶代酒,洞萧一声,吹破大千的静秘;每当昼情午倦之时,解脱衣履,沐浴清他,翡翠双飞,重现乐园的欢慰;或则大雨倾盆,环山飞瀑,赤足而走,大啸呼风;或则浓雪满庭,天地皜素,呼妻与子,同做雪人。啊,这是多么理想的境地哟?——但是,唉,但是,在爱牟现在是不能办到的了。他坐在平台的石栏上只自深深忏悔:“啊,我是被幸福遗弃了的囚人,我的妻儿们都是被我牺牲了!”
嘉华劝他们今年再来,芳坞和尼特都主张立刻搬来,轮流居住,只是爱牟的心中填满了一腔的悔恨,他不愿意再和幸福相邻,他只愿在炼狱中多增加些苦痛。苦痛是良心的调剂,苦痛是爱情的代价,苦痛是他现在所应享的幸福了。他赞成芳坞和尼特迁到此地来,而他终愿独留上海。
天色已渐渐移入晚景了,四人辞别了亭台,从池子西边走去,远远望见瘦苍已经回来迎接他们了。他们匆匆转上大路,改乘人力车先到太湖,路过梅园时还有很多人出园,及抵湖畔时,游人已经绝迹了。
太湖的风光使爱牟回忆起博多湾上的海景,渡过鼋鼍岬后,他步到岬前的岩石下掬了一握水来尝尝它的滋味,但是,是淡的。——“多得些情人来流些眼泪罢,把这大湖的水变成,把这太湖的水变成泪海!啊,范蠡哟,西施哟,你们是太幸福了!你们是度过炼狱生活来的,你们是受过痛苦来的,但在这太湖上只有你们的笑纹,太湖中却没有你们的泪滴呢。洞庭山上有强盗——果真有时,我想在此地来做个喽罗。”
太阳快要坠落了,湖上的七十二峰,时而深蓝,时而嫩紫,时而笼在模糊的白霭里。西天半壁的金光使湖水变成橙黄,无人的鼋鼍岬上已弥满着苍茫的情调。他们被船夫催促,只得又渡回岸来。走到梅园的时候,长庚星已经琳琅地高悬在中天了。
——“这样的梅花有什么探赏的必要!梅花关在园子里面,就好象清洁的处女卖给妓院了的一样。”
爱牟在黯淡的梅花树下只仰头看望星星,旁边嘉华说道:
——“啊啊,大犬星已经出现了。大犬星下正南的一颗大星是什么?”
——“那怕是南极老人罢。”
爱牟这样答应嘉华,但他却远远看见一对男女立在昏茫的旷野里。女的手持着洋烛,用手罩着西北风,免得把烛吹熄,手指被灯光照透,好象一条条的鲜红的珊瑚。男的按着图谱,正在寻索星名,只听女的问道:
——“那北斗星下鲜红的一颗大星是什么?”
男的把头举起来,看了一会又找寻图谱:“唔,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颗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个样子,少女总是淡淡的。”
——“你在说些什么?”女人的声音带些笑意了。只见男的把她手中的烛光吹熄,两人在天星之下拥抱着了,紧紧地接吻着。……
——“爱牟!我们走罢,明天还要到苏州去呢!”芳坞和尼特瘦苍两人在园中各处游了一回走来呼唤爱牟,爱牟才从他的幻觉中回到自己来,他所看见的,只是四年前的他和他的夫人。
——“啊,走罢,嘉华,我们走罢。”
五人同回无锡城外,在一家旅馆中过夜。谈到十二点过后各人都倦于一日的巡游,早沉沉地睡熟了,只有爱牟一人总是不能合眼。他夫人的棉衣今晚不能带来,他夫人的相片来时也忘记了揣在衣包里,这怕是他不能睡熟的最大的原因了。耿耿一夜,左思右想的仍不外是些追怀和后悔,他有时也想到他家中的父母,有时又想到索性到广东去从军,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死一些人,然后被一个流弹打死。假使朝鲜人能够革命,他又想跑去效法拜伦……一些无系统的思想,一直缠绕着他到天亮。
他决心不再往苏州去了。十二点半钟,和嘉华瘦苍在车站上握手告别之后,芳坞和尼特在苏州下了车,爱牟一人便一直坐到上海。他回到上海后,又在他的斗室之中,过送着炼狱的生活了。
1924年3月7日
住在上海的时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赘,临行真是又劳苦了你不少了。我们不能不暂时离开你走,我是只有眼泪。临走的那天,天气还好,但从正午以后海便荒暴了起来,我是真正吃苦了。三个孩子都吐,和儿吐得顶厉害,但是第二天也就好了。我是连动也不能动,就好象死了的一样。到长崎的时候又是大风,雪是落得非常厉害的。到福冈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便在石川家里寄宿,T君也在那里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走了。
在石川家里只宿了一晚上,我们便到御虎家的楼上来了,楼居是很危险的,两天后又要搬家。小孩太多,楼上一个人是不能住的,并且又是破了的房子,真是冷得没法,冷得没法呢。租了一家二十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念到孩子们的份上,家后有菜园,有橘子树,觉得也好。
在回上海以前从我们住过的那家楼上不是可以望见的吗?在邻近有一家有园子的,便是现在所说的住家了。本想先问你后再定夺,但为儿子们设想,很想早一刻移住稍为好一点的房子,所以一个人便决定了,虽是觉得太贵了一点。现刻虽还住在此地,待二三天后便想搬过去了。两天前吃饭是在石川家里吃的,太久了觉得对不住,从昨天起我在自己做饭吃了。
你在上海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只是到此地来后什么人的生活也免得看见。只有这一点好。孩子们都很欢喜的样子。
我依然是寂寞,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种深不可测的孤独的悲哀好象洄漩一样旋涌起上来。
想写的很多,但没安定,随后慢慢写罢。
今天刮大风,下大雪,冷得无言可喻。把佛儿背着,买了东西回来又煮饭,觉得很疲倦。
别来不过才半个月的光景,就好象已经隔了一年的一样。
移到这里以来,每天天气都不好,真是窘人。大前天天气晴了,把三个孩子带着上街去买东西,走过电影馆的时候,孩子们说要看,便引他们进去看了。领着三个孩子看电影,真是再苦也没有的事呢。回来的时候,各人吃了一碗汤面。佛儿真个重起来了,背了半天,夜来身子痛得不能动弹了。
回家来把门开开,又起火,又煮饭,真是累人。岑寂的家中,寒冷的夜气侵人,彻入骨髓一般地冰冷。我的心境是陷在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一种状态里面的。夜到深时也不能睡熟,孩子们因为倦了,都立刻睡熟了。还是只有孩子们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不安的心事。
好象想写的东西很多,但一写起来,这样也想不写,那样也想不写,结局是什么也不能写下去了。这是因为想起你在上海的生活的缘故。真的,我们的生活真是惨目!我们简直是牛马,对于十分苛酷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马,人是没有些儿同情,没有些儿怜悯的一样。我们的生活简直是一点同情一点怜悯都不能值得!周围的人都觉得可羡慕,他们只在被赋与的世界里面享着幸福过去。
象我这无力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被赋与了的东西也被剥夺了,把持着了的东西也失掉了,我以后正不知如何。在心里留剩着的只有这么一点,女人到了三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迟了!我是只有这一点遗恨。孩儿的爹爹,我对你说,人生是怎样短促的哟!这虽是什么人都知道的事体,但是实际上浸润在身心的很少。
我们走后你在上海生活是怎么样呢?
不知道为何,只是这样被深不可测的悲寂恼乱着。从上海带来的点心,也在今天吃完了。夜半不能睡的时候,一个人取出来吃。每天每天,想起来的时候便吃,也把给孩子们吃。虽是稍稍顾惜着在吃,但是到了今天,蜜枣也吃完了,什么也吃完了。
这边百物都贵,贵得没有道理。小小的鲷鱼一匹也要两毛钱,孩子们一人不把一匹给他们的时候又不够。佛儿是吃的牛奶和粥。
今天风很大,简直不能外出。
随后再写。
爱牟夫人回日本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转来。起初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在这样摇曳不定的情绪之下苦恼着的爱牟,在今天的早晨,突然才接到了这么一封长信。他急切地揭开信来展读,比得着天来的灵感时还要急切,还要兴奋的一样,他的心尖很迅速地战颤起来,胸腔紧张得好象要爆裂,读一句,他的眼鼻只是涨痛一次。
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异常草率,儿童们在旁边骚扰的光景,可以历历看取。信的后半部更显然是夜深人静后牺牲着睡眠的时间写的了。一面忧心着目前的儿童,一面又挂念着海外的丈夫,应该欢聚的生活却不能不为生活分离,应该乐享的爱情却不能不为爱情受苦。做母亲的心,做妻的心,一时把她引到天涯,一时又把她引回尺咫。在空间的陋室中,在冷寂的夜气中,一个孤独的女人,描写着生离的恨绪。这在不关休戚的人看来,就如象在杀入场上看见了处决死囚,看见了别人的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倒可以感受些鉴赏悲剧的快感。但在身当其事的人,在与当事者有切肤之痛的人,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眼泪,是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的了。
“啊,他们是安抵了福冈,只有这一点是可以感谢的。”
爱牟一面读着,一面潜潜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读一遍,他的眼泪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而为一体。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与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什么都被人剥夺了,什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呢!”
“不错,人生原是短促的!我们为空间所囿,我们为时间所囿,我们还要受种种因袭的礼制,因袭的道德观念的欺辱,使我们这简短的一生也不得享受一些儿安慰。我们简直是连牛马也还不如,连狗彘也还不如!同样的不自由,但牛马狗彘还有悠然而游,怡然而睡的时候,而我们是无论睡游,无论昼夜,都是为这深不可测的隐忧所荡击,都是浮沉在悲愁的大海里。我们在这世间上究竟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绞尽一些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替大小资本家们做养料,为的是养育儿女来使他们重蹈我们的运命的旧辙!我们真是无聊,我们的血简直是不值钱的克菜水,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去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我就当讨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我爱人的丈夫,做我爱子的慈父。我无论别人骂我是什么都可以,我总要死在你们的怀里。女人哟,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你所把持着的并未失掉,你所被赋与的并未被人剥夺呢!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里去,实在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把三个儿子杀死,然后紧紧抱着跳进博多湾里去吧!你请不要悲哀,我是定要回来,我们的杂志快要满一周年了,我同朋友们说过,我只担负一年的全责,还只有三四十天了,把这三四十天的有期徒刑住满之后,无论续办与否,我是定要回来的。我们是预备着生,还是预备着死,那时候听你自由裁决,我是什么都可以。你所在的地方我总跟你去。无论水也好,人也好,铁道自杀也好,我总跟你去。我誓不再离开你一刻儿,你所住的地方我总跟你去的呀!……”
他自言自语地发了一阵牢骚,又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阵眼泪,他的意识渐渐清晰了起来。他是在一个小小的堂屋里踱来踱去地步着。时候已近午后两点钟了,淡淡的阳光抹过正面的高墙照进窗来,好象是在哀怜他,又好象是在冷笑他的光景。堂屋里除去一些书橱桌椅之外,西壁正中钉着一张歌德的像,东壁钉着一张悲多汶的像,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都带着严厉的面孔好象在鄙夷他的样子。“你这样意志薄弱的低能儿!你这忧郁成性的白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无聊,你的思想是怎样的浅薄,你的感情是怎样的自私!象你这样的人正是亵渎艺术的罪人,亵渎诗的罪人!……”这种尖刻的骂声,好象从两壁中迸透出来,但是他也全不介意,他只是在堂屋中踱来踱去地步着。“悲多汶哟,歌德哟,你们莫用怒视着我,我总不是你们艺术的国度里的居民,我不再挂着你们的羊头卖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们告别,我是要永远同你们告别。”他顾盼着两人的像片自语了一阵,不禁带着一种激越的声音又讴吟了起来:
去哟!去哟!
死向海外去哟!
文艺是什么!
名誉是什么!
这都是无聊无赖的套狗圈!
我把我这条狗儿解放,
飘泊向自由的异乡。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哟!去哟!
死向海外去哟!
家国也不要,
事业也不要,
我只要做一个殉情的乞儿,
任人们要骂我是禽兽,
我也死心塌地甘受。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哟!去哟!
死向海外去哟!
火山也不论!
铁道也不论!
我们把可怜的儿子先杀死!
紧紧地拥抱着一跳,
把弥天的悲痛同消。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他反反复复地讴吟,起初只是一二句不整饬的悲愤语,后来渐渐成了这么一首歌词。这是文人们的一种常有的经验,每到痛苦得不能忍耐的时候,突然经一次的发泄,表现成为文章,他的心境是会渐渐转成恬静的。爱牟也玩味到这种心境上来了。不怕他的心中,他的歌中,对于文艺正起了无限的反抗,但他却从衣包中搜出了一枝铅笔来,俯就桌上,把他夫人的来信翻过背面来,便写上了他这首歌词。信上的泪痕还有些是湿的,写时每为铅笔刺破,但他也不回避,只是刺刺的写,好象他所把捉着了的东西,深恐失掉了的一样。他写好了后,又反复念了一回,他只觉得他的心尖异样的战栗。他索性寻了些信笺出来,想趁势给他夫人写一封回信去,并想把这首歌翻译成日文,写寄给她。但他才要下笔的时候,大门的门环响了。
——“这儿是爱牟先生的贵寓吗?”
——“是的。”
——“爱牟先生在家吗?”
——“我便是。”
——“哦哦!”
两位客人特别表示了一番敬意,但他们的眼光有几分不相信的样子。爱牟把他们请进客厅,他们便各各道了姓氏;其实在他们刚进门时,爱牟看见他们的容貌,听见他们的声音,早就知道他们的来历了。
他们是从四川的C城来的。在两礼拜前C城的红十字会给爱牟拍了一张电报来,仍然要找他去当医生,说不日当派员携款来迎,务希俯就等等,隔不几日爱牟又接到他的长兄由C城寄来一封快信:
爱牟仁棣如面:在叙在渝在万时均有函致弟,迄未得一复,不知吾弟究系何意,总希明白表示。顷C城红会致我一函,附有电稿,特连函送吾弟一阅,便知此中底蕴。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顺询近好,并候晓芙母子旅祺。兄W再拜。2月13日泐。
W仁兄亲家大鉴:爱牟兄准定聘请,月薪四百,现因经费支绌,暂作八成开支,一俟经费充足,即照约开支。即希台端备函转致,诚恐爱牟兄在沪就聘他事。今日由弟电达,缓日派员携款去申迎驾。电稿附呈台览。顺请文安。小弟K顿首。
另外还有电稿一通,和以前所接的电文一样。
他的长兄一向是在C城办事的。红会的事,两年前便替他经营好了。去年在他回国的时候,曾经由红会给他送过旅费到日本去,但是错过了,旅费又打转去了。他回到上海来将近一年,他的长兄在朋友处打听了他的住所,接连写了几封信来,他一概不曾回信。他的长兄爱他的心情很深,他的父母思念他的心情更切,他们都望他早早回家,但他们却不能谅察他之所以不想回家的心理。
十一年前他是结过婚的,结婚后便逃了出来,但他总不敢提出离婚的要求。他知道他的父母老了,那位不相识的女子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把离婚的要求提出来,她可能会自杀,他的父母也会因而气坏。九年前他有一位妹子订婚的时候,他写信反对,发过一次牢骚,说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得一个臭蛤膜,也只得饱吃一口”的话,他的父母竟痛责了他一场,那位妹子也寻了好几次短见。他和他的夫人晓芙自由结了婚,他的父母也曾经和他断绝过通信息,后来念到生了孙子,又才宽恕了他。但他家中写信给他的时候,定还要称他的夫人是“妾”,称他的儿子是“庶子”,这是使他最伤心,最厌恨不过的字面。几次决定写信回家去离婚,但终可怜老父老母,终可怜一个无罪无辜只为旧制度牺牲了的女子。他心里想的是:“纵横我是不愿仰仗家庭,我是不愿分受家中丝毫的产业的,我何苦要为些许形式,再去牺牲别人!父母不愿意离她,尽可以把她养在家中做个老女;她也乐得做一世的贞姑。照人道上来说,她现在的境遇,只是少一个男子陪伴罢了,我不能更逼她去死,使我自己担负杀戮无辜的罪名。”——他怀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便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最能了解他的是他的长兄,但是他的这层苦衷,他却不曾知道。他的长兄只是希望他迅速回C城,但他怎能够回去呢?C城更和他的家挨近了。他想到十一年不见的老父,十一年不见的老母,十一年不见的兄弟姊妹,十一年不见的故乡,他也有终夜不能成寐的时候;但是,要叫他回家,他是不可能,怕永远不可能的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哟,我今生今世怕已不能和你们相见,你们老来思子的苦心,我想起便时常落泪,但是我无法安慰你们,我只好使你们遗恨终古了。我的兄弟姊妹们哟!你们望我的心,你们爱我的心,我都深能感受,但是我们今生今世怕也没有再见的希望了。我们是枉自做了骨肉手足一场,到头我们是互相离隔着到死。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过一次结婚儿戏的女人哟,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别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这样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他自己而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还有一张汇票,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来客的一位把信交了,一位解开衣裳在最里一层衬衫里又取出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红会的信和爱牟长兄的信,内容大抵和前回的相同。只是多说了几句派了什么人来接和送了一千两银子来做旅费的话。爱牟一一把信检阅了,他当面对来人说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汇票他不愿接受,叫他们回四川时一道带回去。
——“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中国医生也还有三十几个呢。”
——“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去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去医,所以人手总是不够用的。”
——“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罢。”
——“吓,吓,吓吓吓……”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人始终不肯拿去,爱牟只得权且收下。他写了一张收据交给来人,他们便匆匆地告别,走了。
淡淡的阳光仍然还照进窗内,客堂里的微尘静静地在空中游戏。爱牟想写信给他夫人的兴头被来人打断,他的意识的焦点又集中到这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上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手里的这么一笔巨款!这对于他隐隐是一个有力的诱惑了。他想:“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C城,那我们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一月有三百二十块钱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块钱作为生活费,也可穷奢极侈。余钱积聚得三五年,已尽有中人之产,更何况将来的薪水还可望增加,薪水之外还可以弄些外润。……”但是他又想到,他二回到C城,便不能不回家;即使不回家,家里人也自会来,那时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自己幸福的将来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他自己的年已耋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他这么思念到他的父母,又不禁浸出了眼泪来。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是最痛怜儿女的人,他还未出国的时候,他的长兄次兄都曾出过东洋,他的母亲思念起他们时,时常流泪,时常患着心痛的情形,他是知道得最详细的。他母亲时常说:绝对再不要爱牟出洋,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再经不着牵肠挂肚了。在十一年前爱牟结了婚,不三天便借故出门,说要上省进学,他母亲亲自送他上船,在船离岸时候还谆谆告诫他:
——“牟儿,你千万不要背着娘,悄悄跑到外国去啊!”
他为他母亲这句话在船上悲痛了好一场,他当时还做过一首诗,而令部还记得: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但是他终竟背着了他的母亲逃到了日本,并且别来便一十一年了!在这十一年中间,他母亲思念他所流的眼泪,正不知道有多少斗斛了。他母亲今生今世不能再见他一面,一定是到死都不能瞑目的了。爱牟时常对他的夫人说:他一生的希望也只想回去再见母亲一面,但是他不能回去,他也不忍回去。啊,旧式的婚姻制度的功果哟!世间上有多少父母,多少儿女,同样在这种磔刑之下,正忍受着多少难疗的苦痛哟!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罢!”
爱牟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把来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他不回C城决心愈见坚定了,他立刻便分别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他的长兄,一封写给红会的会长,把汇票也封在里面,坚决地把关聘辞退了。回头又把他夫人的信来读了一遍,他接着便写一封信去答复她:
晓芙,我的爱妻,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伤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后又是如何伤心,你该能想象得到罢。你的悲苦我是晓得的,我现在也不能说些无谓的话来安慰你;我现在所能说的只有这一句:“我在三四礼拜之后便要回到你那里去了。”我想这一点或者可以勉强安慰你罢。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通忏悔了。我对于文学是毫无些儿天才,我现在也全无一点留恋。我还不能不再住三四礼拜的缘故你是晓得的,我们的杂志要到那时才能满一周年,我对于朋友的言责是不能不实践的。
今天刚接到你的信后,四川的C城红十字会派人来接我们来了,大哥他还不知道你和儿子们都回日本去了呢。红会送了一千两银子来做路费,我拒绝了它,同时把路费也给它送回去了。我拒绝它的原故,想来你当能了解我罢?我固不愿做医生,我尤不愿回C城。C城和我家乡接近了,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我不愿我的父母到老来还要作我的牺牲。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为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请你原谅我罢!我永远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总要跟你来,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愿。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体,前几天我到无锡去过一回,去年夏天无锡的朋友们不是说替我们找到一个住所吗?那个住所真好,我此次跑去看了来,很可惜去年我们没有搬去。倘使去年我们是去了的话,我们的生活,或许不会如许落寞,你也不会转回日本去了。但是,过往了的事悔也是来不及的。我现刻对于生活的压迫,却一点也感不着什么了,我有解决它的一个最后的手段,等我到日本后再向你说罢。最痛快的事情是我今天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蹂躏了一次——真个是用脚来蹂躏了一次。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我到日本去后,在生理学教室当个助手总可以罢,再不然我便送新闻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采取我最后的手段了。到日本后再说。
为我抱着孩子们多接几个吻。
他草率地把几封回信写完之后,时候已经将近四点钟了。身上好象放下了莫大的负担,心里也疏畅了许多,只是两眼觉得异常干涩,他便把纸笔检好,又去打了一盆冷水来洗了一次脸,把几封信揣在衣包里,打开后门出去。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稣钉死在Golgotha山上的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复活在上海市上了。
1924年3月18日
相关文章
郭沫若诗两首教学反思7则2023-06-14 13:25:43
归园田居六首2023-06-14 21:42:38
归园田居扩写2023-06-13 08:18:02
归园田居语文教案2023-06-10 15:11:24
归园田居教案设计 高中2023-06-12 15:08:32
郭沫若诗两首基础知识题及答案2023-06-04 20:45:58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对比哪个好(排名分数线区2024-03-31 16:25:18
河北高考排名237950名物理能上什么大学(能报哪些学校)2024-03-31 16:19:2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山东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5:16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12:5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3-31 16:09:19
安徽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招生人数和最低分2024-03-31 16:04:52
醉翁亭记主旨句2023-06-17 14:25:36
醉翁亭记读后感(四篇)2023-06-05 01:46:10
醉翁亭记教案范文集合十篇2023-06-19 05: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