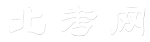消失的老舟美文
一
一直站在徒骇河岸边一块突兀高埂上的那只苍鹭,不知什么时候振翅而飞,消失在芦花深处,再也难觅行踪。我呆呆地望着此刻变得更加苍凉的河水,心中怅然若失。徒骇河两岸都是风,河的上空也是风。风在两岸把刚刚秀齐了紫红色花絮的芦苇,吹得起起伏伏,刷刷作响,也把徒骇河水吹得浪花翻滚。浪花的上空有几只红嘴鸥在飞舞,不时从空中扎向水面,叼起一条小小的鱼儿,翅膀尖和脚蹼带起一串水珠,飞到空中。红嘴鸥的叫声单调而嘶哑,远没有去年我在此地听到的摆渡交响曲那般动听。
心中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带着希冀而来的我,没有看到那只瘦瘦的苍鹭,没有看到和苍鹭同样消瘦的老周,也没有看到摆渡上和老周谐音的那艘被我称为“老舟”的木质渡船。
自然也就听不到老周那沙哑却不失韵味的渡船号子,听不到“老舟”那卯榫深处贴着徒骇河水发出的“咿咿呀呀”的乐声了。
老周的脸是黑的,一种带紫红色的黑。他瘦瘦的面颊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皱纹便挤在一起,变成一种类似京剧花脸脸谱般的图案。老周很瘦,瘦得像站在徒骇河岸边一块突兀高埂上的那只苍鹭。老周的双手满是青筋,和脸色同样的黝黑。老周的声音有些沙哑,如同那只苍鹭抻着长长的脖子叫出的声音。但这声音很有穿透力,能穿越徒骇河悠悠的河水,在对岸的芦苇荡里久久回荡。老周的号子声与“老舟”那卯榫深处发出的“咿咿呀呀”的响声交织在一起,便是徒骇河下游最后一个渡口上最动听的音乐。这音乐到了高潮的时候,便是老周拉着钢纤带着“老舟”和满船的过河人走到了徒骇河中央。浪花打着“老舟”的两舷为老周伴奏,风儿吹拂着两岸的芦苇为老周伴奏,白鹭红嘴鸥还有林鹬鹤鹬青脚鹬反嘴鹬黑翅长脚鹬一起鸣叫,为老周伴奏。这些鸟儿一边鸣叫一边飞舞,把徒骇河上最后一个渡口变成了一个场面宏大的舞台,把老周变成了一场盛大演出中的主角。这时候老周的黑脸上泛着红光,老周成了徒骇河下游河心中众人钦慕的英雄。
那只站在徒骇河岸边一块突兀高埂上的苍鹭,也在此刻腾空而起,掠过河中央的“老舟”上空,扶摇直上,一直飞到白云深处。
二
我就是在这音乐声中认识老周的,那时候我在县里挂职。
去年的深秋,已经过了寒露。一个冰凉的清晨,我沿着徒骇河东岸一路向北,去寻找那片红海滩。出了县城,却是大雾弥漫,公路两边能见度很低,高高低低的庄稼和芦苇在雾中影影绰绰,如梦如幻。也许因为我起得早,也许是天气原因,出了县城以后就没碰到一辆车,也没看到一个行人。我打开防雾灯,光柱照出几十米,便消失在茫茫的白色之中。我已经迷失了方向,幸好我知道出了县城到海边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岔道,便小心翼翼慢慢前行。
这样孤寂地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听到了前方传来一群人说话的声音,一会儿又有拖拉机发动的声响,便停下车来,想看个究竟。过了几分钟,从左边徒骇河滩里的芦苇丛中,开出来三辆拖拉机,每辆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两三个头上包扎着红头巾的妇女。从河滩到公路有个坡,拖拉机一阵吼叫,突突突冒着黑烟爬了上来。头一辆车上的司机看到浓雾中我的车灯,就把速度降下来了。我赶紧上前搭讪,问这是什么地方。那司机咧嘴一笑,说这是鸠山渡口。
我有些吃惊,没想到在这芦花深处还藏着一个渡口。我曾经沿着这条路走过好多次,但这个渡口却从来没有留意过。曾经读过我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文友写过一篇的散文,叫《最后的摆渡》,没想到写的却是这里。
索性先不向前走了,慢慢把车拐下坡,沿着拖拉机驶来的方向往河边走,我要去看看这个“最后的摆渡”。与对面驶来的又一组三辆拖拉机会车以后,我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在芦苇的夹持下看到了徒骇河水,看到了正在驶向河对岸的那条渡船。
渡船上只有一个苍老的身影,两只手拉着一条钢纤,离彼岸越来越近。就在对岸的雾中,有十几台拖拉机拍成了一字长蛇阵,一些人站在岸边,等待着渡船的到来。而我这边,静静的,只有我的车伴随着我等待那艘即将回头的渡船。渡船还在对岸,被一层雾笼罩着。有几台拖拉机发动起来,往船上开。我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们交谈的声音,但是不很清晰。
我不着急,抬起头看看天色,雾气淡了许多,头顶上的天空有了一抹蓝色。向东看,太阳出来了,不像平时的朝阳那般绚烂,像一张失血的脸,惨白惨白的,毫无生气。刚才路过的小路两边,浩浩荡荡的芦苇全都白了头,一眼望不到边。雾气依旧缠绕在它们的头顶,那些芦花便时隐时现。刚才过去的那几辆拖拉机和包着红头巾的女人早已没有了踪影,消失在阡陌的深处了。
芦苇丛与河岸交接的地方,是一溜泥滩,窄窄的伸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泥滩上有许许多多的小小洞穴,我知道那是毛蟹的家。走近了仔细看的时候,有的洞穴是空的,有的似乎有毛蟹在活动。再走近一些,它们便藏进洞穴深处,不见踪影了。离我停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有一处突兀的高埂,两边都是水,高埂上长了一些红色的黄须菜,稀稀落落的。在黄须菜中间,我看到了那一只孤独的消瘦的苍鹭。它伸着长长的脖子,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个雕塑。
我正在出神,耳边响起了号子声,嗨呦嗨呦,嗨呦嗨呦,起先是一个人唱,接下来是好多人一起唱。都是男人的声音,慢慢地听出了歌词,一些鲁北一带老百姓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语言,还有一些带着色的浑话,都变成了歌谣,随着女人们的笑骂声一起传了过来。再仔细听,我听到了“咿咿呀呀”的伴奏声。当声音越来越近的时候,那只像雕塑一般的苍鹭腾空而起,迎着渡船飞去,然后飞向了云天,看不见了。
我看清了那艘渡船,一艘用木头打造的渡船。渡船上满是泥水,并排着三辆拖拉机,四五个男人站在一边用力拉着钢纤,站在中间的是一个黑瘦的老汉,满脸的皱纹,花白的`胡子。他在领唱,两边的几条汉子在和声。船中心站着的是一群包着红头巾的妇女,一边嬉笑,一边叫骂。
渡船靠近了岸边,还有三四米的时候,那老汉从船上跳下来,穿着深桶水靴在河水中,拿一根撬棍用力把渡船驳到了岸边,然后从船上抱下两块木板,一头搭在船舷,一头搭在泥地上。拖拉机手发动了机器,三辆车依次开下来。然后是那些妇女,一个个摇摇摆摆往岸上走,老汉站在水中,不时扶她们一把。
那些女人就笑,说又让老周拉着手了。老汉说,拉着也没感觉,硬的跟个粪叉子一样,没啥滋味。女人爬上汉子们的拖拉机,回头对老汉喊道:“老周啊,晚上等着我啊!”老汉说:“放心吧,见不到你我不散伙!”女人们就骂着笑着,随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的声音走远了。
在女人们的笑骂声中,我知道了这个摆渡的老汉叫老周。
三
老周对我摆摆手,说把车开上来吧。我说我不过河,老周说你不过河大清早冒着浓雾跑到这里来干啥,有毛病吗?我说我是来看看你和这个渡口的,听说这是徒骇河上最后一个渡口了,我想了解一下。老周就裂开嘴笑,说你说对了,把车锁在那里,你上来吧,带你到对岸看看。
我上了老周的船,跟着老周拉起了那根钢纤。钢纤上沾着河水,冰凉冰凉的,滑溜溜的,很难用力。老周不紧不慢,一边拉纤,一边和我唠嗑。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渡口感兴趣。我也问老周,在这里干了多久了?老周说三十二年了,我就掐指算,从一九八一年吗?老周说,一九八零年初冬,我接过这条船的。那时候才刚过三十岁,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呢。转眼之间,就老在这条河上了,人生真是不禁混啊。我问你没搞过别的职业吗?老周说,除了几次生病,几乎天天泡在这条船上,哪有时间去干别的啊。我说这个渡口也很浪漫啊,我听你唱号子呢,还有那些过河的人,和你很亲切啊。老周说都是一个村里的老少爷们,我拉他们过了三十二年的徒骇河,能不亲吗。
我又问这艘船也很老了吧?老周说这是沾化县解放后打造的两条渡船之一,也有五六十年了。原来是县里用的,后来上游修公路,徒骇河上架了桥,就退役了。村里渡口需要一条船,这艘老渡船就运到了这里,几十年来修修补补,一直为鸠山村的老少爷们出力,如今这船也和我一样,老了,你听听它“咿咿呀呀”的叫声就知道了。我就说,你是老周,它也是“老舟”啊,舟船的舟,和你名字一个音呢。老周就笑,呵呵呵,老周陪“老舟”,有意思,看来你是个文化人啊。我就和老周一起笑,问老周对面的村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那些人要在清早匆匆忙忙过河。老周说,这村子吗,叫鸠山,斑鸠的鸠。后来唱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个坏蛋,日本宪兵队长也叫鸠山,上级就把村名给改成永久的久了。他奶奶的,从老祖宗立村到现在几百年了,没想到因为一出戏给我们村改了名字。我说还是斑鸠的鸠好,有文化气息。老周说那是当然,现在村里 又改回来了,可是上边的人还是写“永久的久”,地图上也是,唉!
说着话渡船到了对岸,我登上岸边,那些农人又开始往船上开拖拉机,还有推电动车的,一会船就满了。我对老周说,您先送他们吧,我下一趟再回去。老周对我摆摆手,拉起钢纤,和一群人唱着号子又往东岸驶去了。我爬上河堤向西望去,已经基本散尽了浓雾的不远处,有一个村庄,农舍整整齐齐,清一色的红砖红瓦,许多家庭中还在冒着炊烟,我想着就是老周家的鸠山村了。
回东岸的时候我问老周那些农人为什么要到对岸去种地,老周说原来徒骇河不是从这里走的,是从县城的花家闸向东流,到了1931年治理徒骇河,改了道从套儿河入海,就把鸠山村里的三四千亩土地丢到河东边了。我就说,王母娘娘用簪子划了一条天河隔开了牛郎和织女,那时候的政府挖了一条河隔开了鸠山村里的村民和土地啊。老周说,是啊,其实河东边的土地并不是很好,没有水浇条件一年只能种一季,不是点玉米就是种棉花,收成也一直不是很好。可是我们是农民啊,怎能丢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不管呢?地还是要种,可是王母娘娘还允许七月初七喜鹊搭一座桥让牛郎和织女见一面呢,我们村里的地就只能用我的摆渡拉人去耕种了。你知道吗,这三十多年河东边的三四千亩地的粮食和棉花,都是我用这条“老舟”拉回村里的啊。
我就说是该修座桥了,老周就说你跟上边熟,帮着呼吁一下吧。我说你不怕修起桥来砸了你的饭碗吗?老周就说,你要是帮着争取下来,我会好好的请你弄一壶。
西岸的人和车全都过了河,东岸又来了十几个骑摩托车的汉子。这是在北边盐场下了夜班回家的农民工,也是鸠山村里的人。他们的脸色和老周差不多,黑里透着红,一看就是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的结果。一个汉子给老周递了一颗烟,点上火以后一边抽一边把摩托车推上渡船。我就又跟着上了船,想听听他们在海边晒盐的情况。有个汉子说,这次去盐场值班,半个月没回家了,上了老周的船,就和搂着老婆差不多了。汉子们下了船骑上摩托车跑了,我突然发现,从我到渡口一直到现在,那些过河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给老周摆渡钱。我问老周,他说村里每年补贴三千块,村里人过河就不收钱了,不管来回走几趟,都是义务的。
再次回到东岸的时候,我发现那只苍鹭又站在了原处,伸着长长的脖子一动不动。我对老周说,你看看你这么多年多累啊,瘦得跟那只苍鹭差不多了。老周问,苍鹭是什么?我就指了一指,老周说,那家伙叫“老等”,别说,我还真的和它差不多,老等,有时候要一直等到半夜三更。
四
老周真的经常做“老等”,不管多晚,不管天气如何,只要河东岸还有一个村民没回家,老周就一定在渡口上等。老周经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伸长脖子,翘首以待从河东岸回来的人和车。我在去年的秋冬,又多次去了老周的渡口,听老周讲他几十年来经历的风雨。他每天早上会把从村里出来过河到东岸的人挨个数清楚,每天晚上多少人回来了,还有多少人没回来,老周一清二楚。
忙过了清晨的一阵子,老周的渡口就悠闲了。村里的人下了东坡,都带着午饭,一忙就是一天。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两个季节是农人最忙的时候,也是老周最勤苦的时候。尤其是深秋,看着村里人一车车拉回来的雪白的棉花,金黄的玉米,老周比那些种地的人还要高兴。
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得到闲暇的老周用搪瓷缸子泡上一壶高碎的茶叶,一边喝一边吐茶叶末。等到喝足了水,便开始拿起船头的那张补了又补的渔网,到徒骇河上抡几网。徒骇河很慷慨,为老周献出了数不尽的鱼虾。上游有个花家闸,把淡水截住了,这里的河水是随着海潮上来的,所以捞上来的多是梭鱼,当然还有海虾和梭子蟹。有时候老周会拿着一只桶和一只钩子,去钩一种叫做蚬的蛤喇。到了中午在河西岸的小房子里煮一锅,再喝上二两老烧,倒也自在快活。
就怕闹天气,就怕发大水。可是徒骇河的下游,闹天气发大水是家常便饭。那年八月的一个晚上,一场叫“梅花”台风呼啸而来,风暴潮立刻就把本来不是太宽的徒骇河变成了一片汪洋。风狂吼着,夹着瓢泼大雨从天空倾泻下来。渤海湾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沿着徒骇河倒灌而来,两岸的芦苇全都淹没在水中,平时温柔可爱的徒骇河似乎变成了一头桀骜不驯的怪兽。老周浑身湿透了,可是老周不能离开渡口,因为还有六七个早上过河的村民没有回来。
老周点上了那盏气死风的马灯,挂在船上。尽管灯光微弱,但老周知道,它能给河东岸的人们照亮回家的方向。老周一直等到凌晨两点,雨势稍微小了一些的时候,才看到那几个村民深一脚浅一脚的蹚着水来到东岸。
究竟怎样战胜了河中心的惊涛骇浪,怎样把那些村民安全送到了回家的路上,老周没跟我说。老周还有好多类似的故事,比如村里人得了急病,要去县城医院,老周的渡船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徒骇河上的“120”。
我说老周你是个英雄,老周就咧嘴笑,说狗熊也算不上,村里把这事给了咱,凭良心干吧,都是自家爷们,心里都惦念着呢。我又说老周你真像那只苍鹭,别看平时默不作声,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能搏击风雨,翱翔天空的。老周又笑,说还是叫我“老等”吧。
五
我挂职结束以后,一直想去看看老周。我和老周是有约定的,说等到春天,徒骇河冰雪消融的时候,我带两瓶好酒,老周准备几样下酒的好菜,我们俩在渡口好好喝几杯。老周跟我说了,春天你一定要来,徒骇河里的开凌鮻,是最鲜美的,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拿网去河里捕鱼,一定让你吃个够。
我当然满口应承,还说要老周为我准备毛蟹和蚬,毛蟹炸了吃,蚬肉扒出来,炖豆腐。春节的时候我特意留下两瓶好酒,高度的,准备去看老周。我有些憧憬,想再听老周给我讲那些故事,讲他的“老舟”,讲他的鸠山村和村里的老少爷们的轶事。
我甚至想起了那次和老周说起了鸠山与《红灯记》的渊源,想起了在那艘“老舟”上和老周一起扯开嗓子唱过李玉河的一段戏:“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的骤……”
我深深知道,老周代表着千百年的摆渡文化,代表着一种农耕文明,代表着我的乡人们的淳朴和善良。我必须抓紧成行,和老周在鸠山设宴。
可是假期一结束,单位就忙了起来,学习和工作全挤到一起,就把去看老周的事情忘到脑后了。一直忙到暑假,赶紧驱车前往,一路上眼前晃动着徒骇河满川的芦苇,飞舞着徒骇河上空无尽的水鸟,耳边响着老周的号子声和“老舟”那“咿咿呀呀”的和鸣,我终于到了徒骇河下游的最后一个渡口。
眼前的一切或若隔世。一条笔直的沥青路从河东岸的公路上直插河滩,渡口上一条机器驱动的铁船正发出快乐的轰鸣声,年轻的船主面带微笑从过河人手中接过钞票,招呼人们上船,然后把船驶向了对岸。我看到了船主满面红光,这脸色和一年前我看到的老周的脸色决然不同,原来渡口被承包了。
那只苍鹭没有在徒骇河岸边一块突兀高埂上等着我,满脸皱纹唱着号子的老周不见了,“咿咿呀呀”的“老舟”也不见了。
相关文章
幸福的前奏是孤独美文2023-07-15 17:30:20
给孩子适宜的爱的美文2023-07-13 14:25:29
善缘而始善缘而终的美文2023-07-09 05:23:28
只求落幕无悔美文2023-07-20 15:21:43
带着回忆走,一生无憾伤感美文2023-07-17 02:59:29
经典的哲理美文2023-07-19 11:03:0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对比哪个好(排名分数线区2024-05-05 08:38:37
河北高考排名237950名物理能上什么大学(能报哪些学校)2024-05-05 08:32:42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山东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5-05 08:28:35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5-05 08:26:11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湖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 多少人2024-05-05 08:22:38
安徽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招生人数和最低分2024-05-05 08:18:11
我愿给你举世的温柔美文欣赏2023-07-21 19:32:13
美文欣赏:中彩那天2023-07-14 09:23:27
飘自比利牛斯的圣歌美文2023-07-08 12:19:28